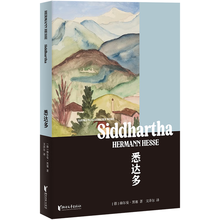乔伊被某人穿过屋子的动静惊醒了。她猛地睁开眼睛,心跳也跟着加快起来。房间里漆黑一片,但屋外已晨光微露。透过玻璃滑门,她能隐约看到门外的露天平台和附近那片红杉林的轮廓。原来是雷伊啊,她松了口气。
电子钟的面板上没有任何显示,看来五天前那场风暴掐断的电力尚未恢复。当时,连几乎完全失聪的乔伊也听到了院里电线杆上变压器爆炸发出的巨响,她母亲吓得往后退缩,她弟弟用手捂住耳朵,接着,一瞬间所有的灯都灭了。
遭风暴袭击的并不只他们一家;狂风以八十五英里的时速横扫整个海岸,所到之处,电力相继中断,交通也瘫痪了,大家都被困住了。往北,一股泥石流堵住了通往莱格特的公路,纳瓦罗河水冲破堤岸,往南淹没了通往克拉弗代尔的道路,其他三条海岸通往内陆的路也被倒下的树木阻断了。如今,只有像她继父雷伊那样熟悉运输木材的交错山路的人.才能够进进出出。
这几天不用每天早起去上学,乔伊都记不得今天是星期几了。星期三吧,她心想,不对,应该是星期四。昨晚他们去了布拉格堡,吃了这些天来的第一顿美餐。因为停电,西夫韦公司冰库里的冷冻肉都化了,他们没把肉扔掉,公司员工把肉切成小片做烧烤,邀请全镇的人一起享用。到现在她还感到饱饱的,睡眼噱咙问,她一边心满意足地笑着,一边纳闷雷伊起那么早干嘛—_这个伐木卡车司机今天没有木材可运,然后她翻了个身,又睡着了。
她再次醒来的时候,天已大亮。她转过身,透过床边的玻璃滑门往外看。她从被子里伸出手来,拨开挡住眼睛的头发,左手的拇指又湿又皱。记忆中,醒来发现手指湿湿的已经是很久以前的事了,她曾觉得自己终于过了吮手指的年纪而颇感安慰。她用右手抓住左手的大拇指,把它像海绵一样挤了又挤。
今天终于迎来了五天来久违了的阳光,阳光穿过树丛,斜斜地照在屋子后面的小径上;雨滴还在红杉树的叶子上打着转,在光线的照射下仿佛圣诞节的彩灯一样闪闪发光。她躺在床上注视着这一切,等拇指上的褶皱消失了再起床,这样母亲就不会发现她又吮手指了。她努力回忆究竟梦到了什么,让她在睡梦中如此焦灼。这是县里的心理学家教她的,要直面恐惧,不要被它们吓怕了。
一阵微风拂过红杉树叶,但是雨滴依旧悬在叶子上。她想象自己就是从天空落下的一粒小水珠,如果最终没有绿叶可以落脚,就只是个过客。她专注地看着一粒水珠,仿佛是在守护它似的,直到一阵稍强的风把它吹落到露天平台,摔得粉碎。
乔伊又看了看她的拇指,已经恢复得差不多了。为什么我会吮手指呢?她又暗自思忖。我在自己的房间里,我很安全。弟弟卢克出生后,她就一直跟他共用着前面的一间卧室。直到四个月前,工人们加盖完了第二层,雷伊和她母亲搬到楼上住,他们原来的卧室就腾出来变成她的了,从这问房可以看到小溪和林木掩映的峡谷。
在丧失听觉之前,她爱听松树间风的呢喃声,虽然她无从知道红杉树林里的风声有何不同,但当她看到摇曳的树枝时,声响就在她脑海中浮现出来,仿佛能听到似的。即便是耳聋六年半后,她有时还会带着期待醒来,希望听力伴着黎明的到来已经恢复,恢复到和视力一样好。
乔伊并非一点听觉都没有。医生曾告诉过她母亲,她丧失了百分之七十的听力,她依然能听到割草机的轰隆声、链锯的咯吱声、喇叭的嘟嘟声、警报的鸣笛声,以及她弟弟饿时的号啕大哭声和他被弄疼时的尖叫声;除此以外,其他的声音对于她都不复存在。不管怎样,这些年来,她已经开始习惯这种寂静,并在许多方面喜欢这样的寂静。当然,她还是怀念正常人交谈时的闲适韵律、鸟儿的呜声和悠扬的乐声。用眼倾听总是让她想起了笑笑,那个在医院照顾她的护士脸上总是挂着像那个网上的黄色圆形笑脸般的表情,于是乔伊给她取了这个呢称。乔伊的妈妈告诉护士女儿失聪的情况,但经笑笑一诠释,不幸似乎变成了上天赐予的礼物,使一些声音——例如乔伊妈妈的话音、雨声、风在松问的穿梭声——得以永远清晰地封存在乔伊的记忆中,笑笑称之为幻音。笑笑说,她能把记忆中的声音和任何她喜欢的东西联系起来,像落叶和飞扬的蝴蝶那些原本没有声响的也被她配上了乐音。
乔伊握拳头捏着拇指躺了一会儿,凝视着树枝,欣赏它们在摇摆问演奏的美妙声响。这时,她和弟弟曾经共住的卧室门砰的一声被关上了,她为之一惊。屋子里很快就会被一个两岁半的小孩搞得天翻地覆。
乔伊舒展了一下身体,打了个哈欠,把被子拉过脖子,搂作一团。她的房间里冷冰冰的,因为她从来不用暖气,就是开着暖气也觉得冷。她讨厌电暖器的气味和感觉;不论天气变得多严冷,与其开暖气,她更愿意用袜子、保暖长裤和一层层暖和的毯子把自己裹严实。未经电暖器加热的空气能让她尽量不去想锈迹斑斑、热不可耐的房车和在严冬闷热的空荡荡的寓所。
虽然她爱在冰冷的房间里睡觉,却不喜欢起床时冷飕飕的感觉。她抽身下了床,迅速拉起床罩盖好枕头,然后蜷着身子,手塞在胳肢窝里,奔向生着柴炉的会客厅。她往下瞥了一眼,看看盥洗室的灯是否亮着,接着想起来停电了。乔伊慢慢推开门,怕里面有人。壁挂式烛台上燃着一支蜡烛,烛台是她母亲在上次停电时买的。
“嗨。”她说着走进厨房,刷刷牙用的瓶装水还拿在手里。
她母亲从科勒曼双头炉边转过身来,微笑着。
……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