仲夏时节,我遇到了唐纳德.希蒙达。做了四年飞行员,我从未发现还有第二个人做着和我同样的事情:乘风起飞,从一个小镇到另一个小镇,向镇上的居民兜售飞行体验——如果有谁肯付三美元,我就让他占据这架老式双翼飞机的一个座位,带他飞行十分钟。
但是有一天,当我飞到伊利诺伊州的费里斯北部上空,从“舰队”驾驶舱向下望时,发现一架金色与白色相间的“空中旅行4000”老式飞机,正向一片赭黄夹墨绿的干草地上降落,动作相当娴熟。
我的日子过得自由自在,只是偶尔有些寂寞。看到那架飞机在那里降落,我想了想,觉得那片草地还算合适。于是我收小油门开始减速,进行满舵侧滑,“舰队”和我慢慢向“空中旅行”旁边的地面降落。风穿过两片机翼之间的张线,发出柔和的声音,老式引擎带动螺旋桨悠悠地旋转着,慢吞吞地发出咔嗒咔嗒的声音。为了看得清楚些,我戴上了护目镜。玉米秆上的绿叶密如丛林,在机身下随风伏倒,飒飒作响。一道篱笆从眼前一闪而过,远远的前方可以望到刚刚收割的干草。我把驾驶杆往后拉,调整方向舵,飞机停止了侧滑,在地面上方打了个漂亮的小拉平。干草轻轻擦着轮胎,然后就听到了机轮碰撞硬地面发出咔喇喇的声音,熟悉而冷静。“舰队”着陆滑行,越来越慢,越来越慢,随后进发出一阵声响,停在了那架飞机旁。收油门,熄火,螺旋桨咔嗒咔嗒轻响着,在七月的静谧中停止了转动。
“空中旅行”的飞行员坐在干草上,背靠他飞机的左轮,看着我。
我也看着他,足有半分钟,想探究他那平静之下的神秘。若是换作我,我可没法如此冷静地坐在那里,看着另一架飞机降落在仅仅十码开外的地方。我朝他点点头,没来由地喜欢上了他。
“你看起来有点孤单。”远远地,我对他说。
“你也一样。”
“我并不想打扰你。要是给你带来了不便,我就离开。”
“没有。我一直在等你。”
听到这话我笑了。“那么抱歉我来晚了。”
“没关系。”
我摘下防护帽和护目镜,爬出驾驶舱来到地面上。坐在“舰队”里飞了好几个小时之后,现在这感觉真好。
“希望你不介意火腿和奶酪,”他说,“火腿和奶酪,也许还有只蚂蚁。”
没有握手,没有任何介绍。
他并不高大,头发及肩,很黑,比他背后的橡胶轮胎还要黑,眼睛很深,就像鹰眼。我喜欢这样一个朋友,换成其他任何人,我都会觉得不舒服。他一定是位空手道大师,正要赶赴某次平静而又激烈的演出。
我接过三明治和一保温杯的水。“你是怎样一个人呢?”我说,“好多年了,我一直飞来飞去,还从未看到其他驾机载客观光的飞行员。”
“其他很多事情并不适合我,”他高兴地说,“我做过机械工、焊接工、钻井工,还开过卡特彼勒推土机。我在一个地方待久了就会惹出麻烦。于是我造出了这架飞机,做起了载客观光的营生。”
“什么型号的卡特彼勒?”从小我就对柴油推土机非常着迷。
“D8,D9。在俄亥俄州,只开过很短一段时间。”
“D9!像一间屋子一样宽敞!双缸复合式发动机,它真的能推动一座山吗?”
“要想推动一座山,另有更好的办法。”他面带微笑地说,这微笑一闪而过,大约只停留了十分之一秒。
我倚在他飞机的下翼边沿,看着他。光线织出幻影,我很难看清眼前这个人。他头顶似乎有一道光环绕,让他身后的景物失去了色泽,成了一片模糊的银白。
“有什么不对劲吗?”他问。
“你遇到了什么麻烦吗?”
“噢,没什么。我这两年一直很享受飞行,和你一样。”
我拿着三明治,绕着他的飞机走。这大概是一九二八或者一九二九年生产的飞机,机身没有任何刮伤。即使是工厂也不能保证生产出的飞机簇新如此,更别说还要把它停在干草中。机身上至少有二十层手工刷涂的丁酸清漆,表面光滑得就像一面镜子,严丝合缝地贴在木质骨架上。驾驶舱下面,有一个用金箔写就的“唐”,装地图的防水袋上的登记信息是“唐·威·希蒙达”。各种仪器都是新拆包装的样子,一九二八年原装。上漆的橡木做成的驾驶杆和方向舵,以及位于左边的油门、油气混合室和点火系统。你不会在其他地方再见到点火系统,即使是保存最好的古董。所有部位都找不到丝毫刮伤,机身没有进行过任何修补,引擎罩上没有机油痕迹,驾驶舱的地板上也没有麦秆的划痕。他的飞机似乎从来没有飞过,只是跨越半个世纪,穿过时间变成了现实。我感到有股奇怪而恐怖的凉意爬上脖颈。
“你载客有多久了?”我问他,隔着飞机。
“一个月左右,到现在有五个星期了。”
……
展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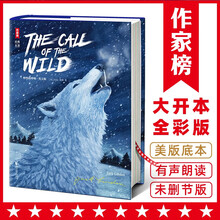



——亚马逊(美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