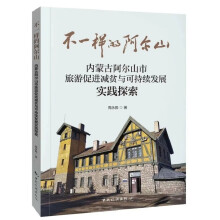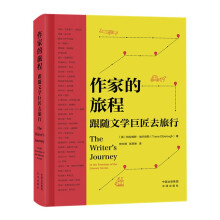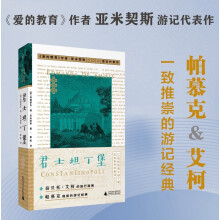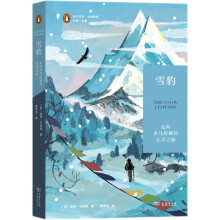八点钟,贝蒂回来了。他找到了马,可把安托万弄丢了。他说,安托万简直是一个稚嫩的孩子,对森林一无所知,独自跑出了他的视线,失踪了。然而,还有更多人与安托万为伍,因为还有几个骑手也迷了路,而老瑞安和他的那伙人也没有回来。
我们等了几乎一个早上,希望这些落伍者能和大部队会合,但他们始终没有露面。队长说,河对岸的印第安人对白人很友好,所以不必过于担心失踪者的安全。但最大的危险是,他们的马匹有可能在夜晚被掉队的奥塞奇人偷走。因此,他决定大部队继续前进,在营地里留下一些殿后的人等他们回来。
我坐在山谷上部的泉水中突起的一块岩石上,自我陶醉地望着眼前水流变幻的景色。我们开始准备出发。马匹从营地周围被赶了进来,骑手们策马奔走在岩石和灌木之间,寻找其他失散到远处的马匹。人们匆忙地收拾着野营装备。水壶和平底锅从一群人手里传到另一群人手里时的吆喝声,人们对倔强难驯的马匹的呵斥声,以及对那些已经装上行李、兀自跑到一边去嚼草的马匹的高声咒骂声,混合成了一片。而在这片乱哄哄的声音当中,我们的小个子法国人托尼什的声音仍然清晰可辨。
号角声骤然响起,该上马出发了。队伍排成不规则的一列沿着山谷前进,穿过稀疏的树林,一路曲曲折折,渐渐消失在树丛之间,可人们的叫嚷声和号角声随后仍不时地传来。殿后者仍留在山谷下方的树下。有些人骑在马上,肩背着枪;其他人坐在火堆旁,或躺在地上,用低低的、懒洋洋的语调闲聊着,他们的马没有上鞍,站在四周打着盹;还有一个骑手利用这片刻的休闲时间,从口袋里掏出一面镜子,把它搁在树干上对着它刮胡子。
喧闹声和号角声渐行渐远,最终消失,山谷恢复了往日的寂静,可偶尔又被火堆旁人群的窃窃低语声,以及树林间某个人沉重的口哨声所划破。秋叶瑟瑟,最轻微的一阵风都能把它们从树枝上刮落,在空中雪花般盘旋飞舞,预示着这一年荣耀的结束。
……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