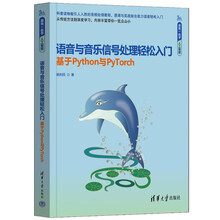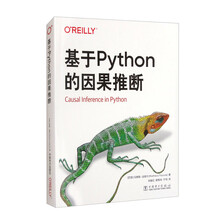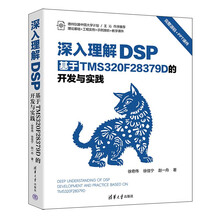最强烈的思想体现在大众和民族之中,体现在最健康和最强壮’的人之中。也许选举是依据重量来运作,如果你可以把小镇里的辉格党和民主党的上百个成员一一过磅,用迪尔伯恩弹簧秤称一称他们的总重量,你就可以准确地预知哪一个党派会赢得选举。总的来说,决定选票的最快的办法就是把市政委员、市长、市参议员放到干草磅秤上去称一称。
在科学上,我们必须考虑到两件事:力量和环境。根据人类持续不断的探索,我们知道鸡蛋是另一种的囊泡——即使在五百年后出现一台更先进的观测仪器,或者一种更精密的显微镜,也会在最后观察到的鸡蛋里发现另一个。在蔬菜和动物的结构组织里,情况都是如此相似!一切的原始力量或痉挛发挥的所有作用只是囊泡!囊泡!确实如此!但起决定性作用的则是环境。德国博物学家奥肯认为,一个处于新环境里的囊泡,一个生存在黑暗中的囊泡,将会变成动物;而在光亮中生存的囊泡,将会变成植物。生存在动物的亲代中的囊泡要经历种种变化,最终产生出奇迹般的力量,衍化为鱼、鸟,或者四足兽,衍化为它们的手、脚、眼、爪。环境即自然规律,自然规律即什么东西你可以做,什么东西你不能做。我们有两样东西——环境和生命。过去一旦我们思考,积极的力量就是一切。现在我们知道,消极的力量,或者说环境,也占其中的一半。自然是个暴虐的环境、粗糙的颅骨、潜藏的毒蛇、笨重如岩石般的颔。它是日常必须的活动,是暴力的倾向,是工具的限制;它像火车头一样,在轨道上强大有力,可是一旦脱离轨道,它只能引发灾难;它又像滑雪,在冰面上自由飞翔,却被束缚在地面上。
自然之书是一部命运之书。她翻动着巨大的页面——一页接着一页——从不回头。她放下的一页是一片花岗岩的地面,一千年后,那儿变成一片石板床;又过一千年,那儿成了一层煤炭;再过一千年,那儿又成了一层泥灰和泥土:出现了植物的形状。她创造了第一批发育不完全的动物、植形动物、三叶虫类和鱼;然后是蜥蜴——粗糙的形体。在它们身上,她只塑造了她未来雕像的轮廓,把她未来君主的美好形象隐藏在笨拙的怪兽的面目之下。这个星球的表面变得寒冷干燥,物种进化,人类产生。可是当一个物种的生命极限到来时,它也一去不复返了。
世界上的种群是历经淘汰的种群,他们不是最佳的物种,但却是现在可以生存的最佳物种。在大规模的种群中,某个种群总是能够抵制住自然的考验,稳定地发展,而另一种群则经受不住自然的考验,这就同社会阶层的更迭相一致。我们知道,在历史上一个民族拥有怎样的影响力。我们看到英国人、法国人和德国人牢牢地扎根于美洲和澳洲的每一片海岸和市场,垄断了这些国家的商业贸易。我们热爱种族中我们自己这一支系的精力充沛、富于进取的习性。我们尾随着犹太人、印第安人和黑人的足迹。我们看到多少人费尽心机,妄图灭绝犹太民族却无功而返。看看诺克斯在《种族残篇》中令人不快的结论吧——这个作家同然草率冲动,令人觉得不满意,但他指控的却是尖锐而令人难忘的真理:“自然尊重纯粹的物种,不是杂种”,“每一种群都有它自己的‘栖息地’”,“把一块聚居地从其所属种族中隔离开来,那么它就会日渐衰落,就像一棵孤零零的野生苹果树一样”。看看地图上的一片片阴影吧,数百万的德国人和爱尔兰人像黑人一样,命运中充满了坎坷。他们乘着轮船越过大西洋,在美洲的大地上颠沛流离,开沟渠,做苦工,使粮食变得便宜,然后过早地躺倒在土地上,化为大草原上一簇青青的野草。
统计学这一门新科学是极其坚硬的枷锁中的又一种桎梏。它是一种法则,即只要人口的基数足够大的话,最为偶然最异乎寻常的事情也会成为一个得以准确计量的材料。人们很难确切地说什么时候波士顿会诞生一个波拿巴式的上校、一个詹尼·林德式的歌唱家,或者一个鲍迪式的航海家。但是,如果有两百万或两亿的人口基数,我们就可以获得一定的精确度。
……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