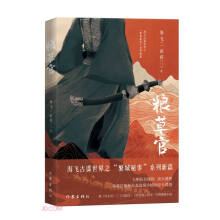妈妈坐在火炉边她的那张椅子里,男孩子们坐在桌边,吃着芮给他们 做的饭。妈妈早上吃的药把她变成了一只猫,一个坐在暖炉边、有气息的 东西,只是偶尔发出一点声音。妈妈坐的是一只老旧的软摇椅,但几乎从 来不摇。有时候她会突然地哼几句毫无关联的音乐,既无调子又无旋律。 但是,白天大多数时候,她一声不响,一动不动。只有头脑里什么模糊的 好事会给她脸上带来一丝残存的微笑。她是博蒙特家的人,生在这个家族 ,而且也曾经美丽。即使是她现在这副样子,吃药吃得神志不清,头发不 洗不梳,皱纹在她脸上深陷延展,你也能看得出,她跟奥扎克这片崎岖的 土地上所有赤着脚跳过舞的女孩子一样,都曾经美丽漂亮。过去她高挑、 黝黑、可爱动人,但后来神志就破裂了,碎片撒得到处都是,而她也就任 其四处散落了。 芮说:“赶紧吃完,汽车就要来了。” 这屋子是1914年建的,天花板很高,唯一的吊灯给所有的物件都投下 分明的影子。影子扭曲的形状遍布地面和四壁,在墙角里凸出来。窗户开 得很高,去年冬天贴在玻璃外面的塑料纸碎成一缕一缕的,在风里抖动着 。屋里的家具是博蒙特家祖父母一辈活着时送来的,妈妈还是个孩子的时 候就用上了。疙疙瘩瘩的垫子和破旧的布面至今还保留着爷爷烟斗的气息 ,和一万个灰尘仆仆的日子。 芮站在水槽边洗盘子,望着窗外陡坡上光秃秃的树、隐约可见的石崖 ,还有那条泥泞的小道。风暴将枝桠推来搡去,从窗框边呼啸着吹过,尖 叫着窜进烟囱。天向着峡谷里压下来,低低的,阴阴的。风剧烈地刮着, 似乎就要将天撕裂开,下起雪来。 桑尼说:“这袜子都臭了。” “你能不能将就着穿穿?就要误车了。” 哈罗德说:“我的袜子也臭了。” “能不能拜托拜托拜托你们把他妈的袜子穿上!行不行?啊?” 桑尼和哈罗德年纪差了十八个月。两人几乎总是形影不离,就连并着 肩四处跑也会同时突然转弯,不用一句话,就那么诡异而本能地一致,仿 佛一个跳跃的双引号。年长的是桑尼,十岁,身体里淌着兽性的血,强壮 、敌对、直接。他头发的颜色就好像橡树的落叶,年轻的拳头十分有力, 在学校里常和人打架。哈罗德跟着桑尼,也想学他的样,但却没有那种报 复心和强健的肌肉,总是一身淤伤地回到家里,丢尽了脸。 哈罗德说:“芮,这袜子也没有那么臭。” 桑尼说:“不,是臭的。但这也不要紧。还是穿着吧。” 芮最大的希望就是,即便毕生无趣,毫无善心,骨子里透着恶意,这 两个男孩子要能活到十二岁,就可算是奇迹了。多利家有那么多孩子都是 这样给毁了,下巴上还没来得及长毛,就被调教得惯于在律法之外游走。 他们所遵守的戒律,主宰了法律之外的生活,浸透鲜血,不谈悔恨。姓多 利的有两百,另外还有那些姓洛克伦、博舍尔、坦克斯利和朗安的,也算 是多利家的亲戚,就住在这条峡谷外方圆三十多英里的地方。有些人过着 守法的日子,但许多人并不这样。即便是那些守法的,骨子里仍旧是多利 家的人,在关键的时候或许就能帮上大忙。那些脾气更硬的,彼此相处时 也粗野得很,若遇到敌人,则会让他吃足苦头,毫不顾及镇上的法令和习 惯,全是互相依仗。有时候,芮给桑尼和哈罗德晚饭做的是燕麦粥,他们 就哭闹着要肉吃。一面把盘里的吃得干干净净,一面吵着要那些得不到的 东西,像欲望和需求的龙卷风,叫芮心里害怕。 “去,”她说,“把书包拿着,赶车去。把帽子戴上。”P4-6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