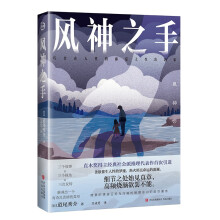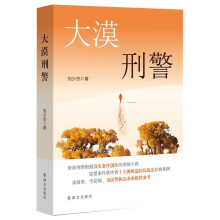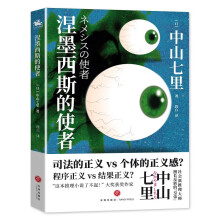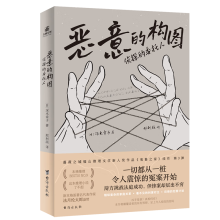第一章 在萨福克郡海岸漂浮着的一艘小船的底部放着一具没有手臂的尸体。那尸体看起来像是一位中年男士的,从尸体上看,死者的身材很矮小,他身上穿着有细条子花纹的黑色西服,与他那瘦弱的身躯极为相称,感觉穿起来就像活着时那样,十分优雅。手工制作的鞋上除了鞋头处的磨损外依然闪着微光,丝质的鞋带打成了一个结。他的穿着谨慎小心,符合这个城镇对已故者,也就是这个不幸的航海者所持的传统观念,他们关心的不是这个孤独的海洋,也不是这次死亡本身。
那是十月中旬的午后,目光呆滞的双眼看到的是西南的微风卷过几片云彩,遮住了湛蓝的天空。没有桅杆的木棺材被缓慢地推到了北海的潮水中,以至于尸体的头部不停地晃动,像是处于长眠状态无法醒来的人。这个男人有着一张极其普通的脸,无论是活着还是已经死去,他都有着空洞的神情,让人为之感到悲痛。亚麻色的头发稀稀落落地分散在他高凸起的前额上,他的鼻子很高耸,发白的鼻梁骨像是要刺穿他的血肉;他的嘴唇很薄,嘴很小,微张着,正好露出两颗突起的门牙,使他整个表情看起来像极了兔子死去时的表情。
他的双腿僵直地夹紧着,被固定在了甲板的中央,前臂放在了小船的横坐板上。双手在手腕处都被截断了,但并没有流血。前臂上流下的几滴血在蓬乱的头发与横坐板之间织出了一张黑色的网。横坐板已经被染了色,像是曾经被用作了剁肉板。除了那唯一流血的地方,尸体的其他部位和小船的甲板上再无其他血迹了。
他的右手已经被完全截断了,露出骨头的地方闪着白光;左手看起来就血肉模糊,伤口边缘有骨头的碎片,萎缩的肌肉上露出碎骨的尖头。夹克衫的袖子和衬衫的袖口都被拉了起来,一对金色的链扣在衬衫的袖口处悬挂着,慢慢旋转,在秋天阳光的照射下发出微光。
小船已经掉漆并且蜕皮了,像是在一望无际的海洋中独自漂浮的被遗弃的玩具。地平线上,只有一个小船的轮廓行驶在雅茅斯航线上;除此之外,视线内就一无所有了。大约两点钟的时候,一个黑色的圆点划过天际,俯冲向大地,身后留下一长串痕迹,发动机发出的巨大响声划破了整个天空。之后,响声渐渐消失,除去海水击打小船的声音和偶尔传来的海鸥的叫声,周围又回到一片寂静。
突然,小船开始剧烈地摇动,过了一会儿才慢慢摇晃,趋于平稳。就像感到岸上有一股强烈的力量在拉着一样,小船开始向着岸边驶去。一只黑头海鸥向船首飞去,并停留在了那里,像个傀儡一样,一动不动,之后带着狂野的叫声在尸体的上空盘旋。海水缓慢而持续地向船首扑去,小船带着会令人窒息的货物向岸边驶去。
第二章
当天下午快到两点的时候,达尔格里什警长开着他的库珀一布里斯托尔停在了柏林斯波夫教堂外的草地边上,一分钟后,车穿过北面小教堂的门来到了位于萨福克郡的最令人舒服的闪着冷白金属光泽的小教堂里。他是在去位于邓尼奇南部的蒙克斯米尔的路上,要和他未婚的姑姑去度过一个为期十天的假期。他的姑姑是他唯一的亲戚,而这一站也是他在路上休息的最后一站。在他从伦敦的思迪公寓出发前,他十分兴奋,他并没有选择路过伊普斯威奇直接到达蒙克斯米尔,而是选择穿过北面的切姆斯福德来到位于萨德伯里的萨福克郡。他在梅尔福德吃了早饭,然后向西部的拉文汉姆缓慢行驶,沿途路过了很多绿色或金色的未经破坏未加修饰的原始村庄。要不是他心里一直有个令他j1)神不安的忧虑,可以说他的心情该是与当天的风景极其相符。在没有打算度假之前,他一直在刻意回避有关于他个人的一个决定。在他再次回到伦敦之前,他必须决定自己是否要向黛博拉·瑞希可求婚。
很不合理地说,如果他不知道她能够给出确切答案的话,那么这个决定要容易得多。他面临的是是否要改变现在这个令人满意的现状(无论如何,目前他还是很满意的,虽然他不敢保证现在的黛博拉·瑞希可是否比一年前快乐)去寻找一个答案,而他认为,无论结果是什么,这个答案势必会把他们两个带到一个不可挽回的局面。然而,那些勇于公开承认婚姻中的不快的夫妻也还是可以过得很幸福。他还知道很多类似这类灾难的事情。他知道黛博拉·瑞希可不喜欢,甚至可以说是讨厌他的工作。这一点并不让他吃惊,也不是特别重要。这个工作是他自己的选择,他从没要求过别人的认同,也不需要别人的鼓励。令人生畏的前景是每次的加班,每次的紧急任务都要排在带有歉意的回电的前面。当他在带有拱形横梁的屋顶下面来回踱步的时候,闻到打蜡的屋子发出的味道,花的香味和潮湿的古老的赞美诗书籍发出的气味,这一切让他觉得此时此刻他已经完全得到了他想要的东西,而这些东西是他觉得永远不敢奢求的。这极容易让一个有智慧的人感到失望,也会让人感到极度不安。失去自由并不会让他感到不安;经常会让人尖叫咆哮的是人们完全没有了自己的空闲时间。使人更无法面对的是会失去自己的隐私权。即使是失去个体的隐私权也同样令人无法接受。他把手指放在教堂里雕刻着花纹的15世纪的读经台上,试着勾勒和黛博拉·瑞希可一起在公主山公寓的生活画面,那时他的生活里不再有急切等待接见的访客,只有他唯一的经法律认证的亲属。
……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