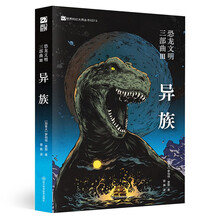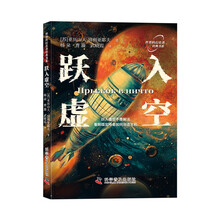13点17分,艾克谢林茨把我叫去。他没有抬头,我只能看到他那满是白色老年斑的秃顶。这说明他非常焦虑,而且情绪不好。但这不关我的事。
“坐。”
我坐下了。
“要找一个人……”刚一开口,他就突然停住,很久没再开口,眉头紧锁,面带怒容。可以猜想得到,他对自己刚才讲的那句话不满意,要么措辞不佳,要么内容不对。他很讲究表达的绝对准确性。
“要找什么人?”我问道,想帮他摆脱这种语言上的尴尬。
“列夫·维亚切斯拉佛维奇·阿巴尔金,一名进步使者。前天从萨拉克什星极地站离开,来到了地球。到达地球后,他没有登记注册。我们必须找到他。”
他又停顿了,第一次抬头看了我一眼。他的眼睛圆圆的,绿得不大自然。他显然很困倦。我明白,问题严重极了。
严格说来,阿巴尔金是一名制度破坏者。一般情况下,进步使者返回地球后可以不登记注册,因此,他是否注册登记未必会引起委员会的注意,更别说让艾克谢林茨亲自抓捕他了。这时,艾克谢林茨显得疲倦极了——我觉得他似乎马上就要靠到椅背上,呼一口气,以一种轻松的口吻说:“好了。对不起,这件事我自己干算了。”——这种情况是有过的。虽然不多,但是有过。
“有理由相信:’’艾克谢林茨说,“阿巴尔金是躲起来了。要是十五年前我追问过一句他是什么人生的就好了。现在过去了十五年,错过了追问的良机。
“你一找到他就通知我,”艾克谢林茨继续说,“不许有任何暴力行为。总之,不能施暴。找到他,监视他,通知我。要求就是这些,不多也不少。”
我赶紧点头,表示充分领会。但他还是死盯着我不放,我只好故作镇定,认真地重复了一遍他的命令:
“我应当找到他,盯住他,然后通知您。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试图抓捕他、惊动他,更不能和他交谈。”
“是这样。”艾克谢林茨说,“现在谈下一个问题。”
他把手伸进桌子侧面的抽屉——任何一个理智健全的人都会把珍贵的信息存储器放在抽屉里——从里面取出一个沉甸甸的东西。我马上想到了弘纪语中那东西的名字,确切地说,就是“文件匣”。不过,直到他把它搬上桌摆在面前,又把骨节粗大的长手指放在上面,我这才敢叫出来:
“文件匣!”
“别打岔!”艾克谢林茨厉声说,“注意听好。委员会里没有人知道我对他感兴趣,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应刻有人知道。所以你只能自己单干,没有助手。你的小组现在转归克拉夫吉亚负责。你必须当面向我报告,无论如何不能破例。”
必须承认,我惊讶万分。这种事以前从来没有发生过,我在地球上还没接触过级别如此之高的秘密。说实话,我甚至连想都没有想过,竟然会有这种事。所以,我斗胆问了一个相当愚蠢的问题:
“‘无论如何不能’,这是什么意思?”
“‘无论如何不能’,就是说,在这种情况下‘无论如何不能’。参与此事的还有其他几个人,但是,既然你和他们永远不会见面,那么实际上,他的情况也就只有我们两个人知道了。当然,在找人的过程中你必须和很多人谈话,你可以编故事给他们听,你自己编。没有故事好编的时候,你就跟我说。”
“是,艾克谢林茨。”我顺从地说。
“然后,”他继续说,“看来,你得从他的社会关系人手。至于他的社会关系,我们掌握的全部材料都在这里。”他用手指敲了敲文件匣,“虽然不太多,但有刚开头你需要的东西。拿去吧。”
我拿过文件匣,我在地球上从没碰过这种东西。不透明的塑料盖上有一把金属锁,盖子上面印着一排洋红色的字——
列夫·维亚切斯拉佛维奇·阿巴尔金
下面不知为什么还有个编号:07。
‘请问,艾克谢林茨——”我说,“为什么用这种形式?”
“因为用别的形式就不会有这些材料了。”他冷淡地答道,“顺便提醒一下,不能用晶体存储器拷贝文件。你没有其他问题了吧?”
显然,这就是说不许再提问题了,他下了一道恶毒的逐客令。本来有很多问题可以现在问,但是,在不了解文件内容的情况下提问,没有太大的意义。不过,我还是冒险问了两个问题:
“期限是多久?” “五昼夜。不能再多了。”
怎么都完成不了,我暗自盘算了一下。
“我是不是应该确信,他现在就在地球上?”
“肯定在。”
我起身要走,他偏偏又不让我走了。他的绿眼睛专注地从头到脚打量着我,瞳孔一会儿缩小,一会儿放大,像猫一样。当然,他很清楚我不太满意这个任务,我觉得它不仅奇怪,而且——温和点的说法是——盲目。但不知何故,他没有再多说什么。不过这会儿,他实在不好什么都不说就放我走。
“你还记得,”他最终还是开了口,“在一个叫萨拉克什的星球上有个名叫西戈尔斯基的人吧,绰号‘云游者’?他追踪过一个名叫马克……的伶俐的毛头小子。”
我记得。
“是这样,”艾克谢林茨说,“西戈尔斯基那时没有找到那个人。但是,我和你应该能找到,因为现在要去的星球不是萨拉克什,而是地球。列夫·阿巴尔金也不是毛头小子。”
“我能谈谈疑难之处吗,头儿?”我说,想解开困扰着我的疑虑。
“干活儿去吧。”他没有答应。
我把安德烈和桑德罗的关系移交给克拉夫吉亚时,他俩很惊讶,都有点儿不死心。最让我担心的是,他们不愿服从命令。我只好大声训斥他们,两人这才一边埋怨,一边用怀疑的目光瞧了瞧卷宗,悻悻离去。他们的注视激起了我一种突如其来的担忧:应当把这个“神秘的文件匣”保存在哪里呢?
我坐在办公桌前,摆放好卷宗,机械地看了看文件目录。七份报告,时长一小时十五分钟——正好是我在艾克谢林茨那里待的时间长度——我认为,自己已经顺利地把全部工作关系移交给了克拉夫吉亚。所以,我就仔细阅读起卷宗来。
……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