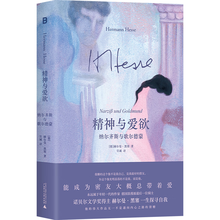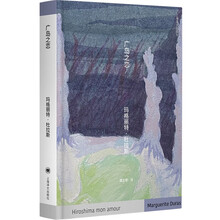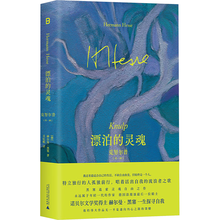索罗门已经不和辛塔也胡一起走路去上学了。他独自从恩陀陀跑下山,再独自跑过城里的街道一直跑到位于希罗·梅达街区的学校。“就是因为你的错,害我没能看到皇帝的狮子!我不要再做你的朋友!”辛塔也胡气鼓鼓地对他说。“这可不是我的错!更何况,你爸爸是军人,你叔叔也是。我才不愿当你的朋友呢!”辛塔也胡习惯参与到各种争斗中去,不论是在学校还是在街上。有一刻索罗门觉得他会扑到自己身上揍他一顿,他会抓他,踢他,拉扯他的衬衫,就像他好多次见到的他对别的孩子所做的那样。但是辛塔也胡只是看着他,什么也没对他说。他朝他背过身,往相反的方向走去。
当索罗门从学校回来的时候,常常会见到他的父亲依旧还在他离开时跟他说再见的地方。他坐在家门前,目光怅然若失。“他们杀死了他。我敢断定他们杀死了他,”父亲重复道,“我不明白他们为什么非要杀死一个受所有人敬仰的德高望重的老人。”在那几天里,大家所谈论的话题除了海尔·塞拉西和另外五十个官员的死就没别的了,索罗门没法想像一个没有了国王的国家会是什么样子,在埃塞俄比亚,没有了皇帝,人们是无法生活的。在他的街区,从表面上看来生活似乎还是老样子。女人们早早出门去汲水拾柴,就跟每个清晨一样。当一天开始的时候,恩陀陀山上的大路与小径上满是各种年龄的女人的身影,她们搬运着水罐和柴火,要么缚在背上,要么牢牢地绑在头上。之后,她们会坐在家门前磨鹰嘴豆和小扁豆,她们把一块石头放在另一块更大的状似米臼的石头上,以缓慢而有力的动作敲打和研磨干豆子。另一些女人则用比她们个子还高的木棍在木臼里面舂打麦粒。但是,一切都不一样了,所有人都心怀恐惧。索罗门听到他的女邻居们谈论几个年轻人的失踪,这些人都是大学生。一个侄子,一个表兄……军人们乘着全副武装的敞篷吉普车全天候巡逻,驾驶员旁的座位上架着一挺冲锋枪。他们的车总是开得很快。晚上,他们会把车停在某家门口,从车上冲下几个男人,他们用脚踹开房门,把那些可疑分子或者拥护旧政权的人从床上拽起,这些人就这么光着脚也没有任何文件地被粗暴地带走了,甚至他们的家人眼看着他们坐上吉普车全速驶离,却不敢提出任何异议。狗在吠叫,除此之外,听不到任何声音。
掌权者要求所有人都去登记。在各个地方,因为任何原因,所有人都有成为敌人的嫌疑。登记一直在持续进行,威胁感也不曾停止。索罗门并不明白什么叫做酷刑。那些女人们说到这个词时都压低了嗓门儿,于是他便没听到余下的故事。
“他们把他在家里藏了三个星期,然后他们就去找他了,肯定是以前的旧同伴出卖了他,不然的话,就说不通他们怎么会找到他的了……”“他们本该把他送出城去的,送到哪个亲戚家里,或者到更远的地方,送到巴哈尔·达尔,或者是贡达尔。”一切都含糊不清。所有的人都在讲着令人恐惧的故事,讲着年轻人躲藏起来以免被逮捕,遭受酷刑和杀害的故事,还讲着因为必须藏匿一个儿子的不安,因为失去一个或不止一个孩子的痛苦而家不成家的故事。
……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