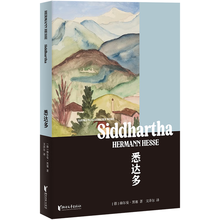所有的信件按照邮戳地区大致做了分类。其中大部分来自乌西马以及土库波里两个省份,还有海梅。来自萨佛以及卡瑞里亚的信件也不少,但是只有一小沓信件来自欧鲁和拉普兰两个地区。对于雷罗南而言,得要亲眼所见,才能证实原来在首都发行的日报在北部并不如在都会区那么普及。来自乌斯托波世尼亚的回复信件也不多,这倒是显示出该地区大致而言比起国内其他地区较少有人自杀。该地区又再一次表现出和其他地区的不同之处,当地人无疑认为自杀是一种背叛乡亲的行为。
这两位男士读了几张明信片,然后开始拆阅第一封信件。绝望从一个个信封里溢出。这些自杀候选人用潦草的字迹写下他们杂乱的信息,完全不管语法结构,看得出来是受到无法控制的力量所驱使,向收件人求援——他们真的不是唯一感到沮丧的人吗?真的是这样吗?这些陌生人真的可以帮助他们吗?
这些信件的署名者一个个都觉得他们的世界在自己的脚下崩塌。他们的心情指数是零,其中有些人的经历是如此令人沮丧,以至于像上校这样目光冷酷的人读了他们的信也不禁要红了眼眶。这些人热烈地回应这则启事,仿佛就像溺水者挣扎着想要攀住落水的稻草。
他们两个发现,要一封封回复这些信件几乎不可能,即便是拆信以及阅读每一封信这样看似不需花太多力气的事,也都显然超乎常人的负荷。在迅速浏览过一百多封信件之后,雷罗南总裁和坎裴南上校已变得疲惫不堪,实在没有力气继续下去,于是他们决定去泡泡澡。
“倘若我们现在决定淹死自己,等于是置六百多条可怜的生命于不顾。他们都可能会因此而自杀。从道德层面来说,我们必须为他们的死亡负责。”雷罗南在浮桥尽头语重心长地说。
“没错……现在已经不是谈自杀的时候了,现在我们已经一肩扛下了捍卫这群可怜人的生命的战争。”上校附和说着。
“这真是一支千真万确的敢死队。”总裁作出结论。
翌日早晨,雷罗南总裁和坎裴南上校光临离西司马最近的一家文具店,为的是要购买一些办公用品,包括:六个活页夹、一台打孔机、一只订书机、一把拆信刀、一架电动打字机、六百一十二个信封,以及两包各五百张的信纸。接着又到邮局去购买六百一十二张邮票。同时将欧司摩·萨尔尼亚侯老师的《海卢奥托百年自杀史》手稿寄回,还附上一张信笺,请他打消自杀的念头,并请他将手稿转寄到芬兰心理健康协会或者类似的机构,那边也许会有人重视这本著作的学术价值。
雷罗南接着去买了些吃的,而上校则负责采购饮料。随后他们便踏上返回鸫鸟湖的旅途。他们已经不再有时间可以懒洋洋地躺在桑拿室里或是去钓鱼。雷罗南抓起拆信刀来拆开每一个信封,坎裴南则充当书记的角色。他依序记下每一个寄件人的姓名和地址,并且给他们编号。这项工作花了他们两天的时间。工作一结束,他们只觉得此刻必须着手进一步研究分析这些信件的内容。将顺序整理好只不过是个开端而已。两位男士很清楚这项工作刻不容缓,十分紧急。有六百多条芬兰人的性命掌握在他们的手中。他们必须快点做出反应,但是单凭两人之力,进度实在是太慢了。
“我们需要找个秘书。”雷罗南总裁叹着气说,当时已经夜深,所有信件都已经拆开并且编了号。
“我可不知道有谁会在盛夏时来当咱们的秘书。”坎裴南上校嘀咕着。
雷罗南突然心生一计,想到在自杀候选人里头一定有人是当秘书的。或者至少有人可以帮他们分担这过量的工作。得从这个角度来关心和处理这些收到的信件。从最近的地方寻找支持是再自然不过的事,于是两位男士便从来自海梅地区的回复信件着手。总裁读了十来封信件,而上校读了大约二十封。
有几位住在豪霍、西司马或是邻近地区的农民写信来说明他们的自杀念头,但是庄稼汉不一定能够胜任办公室的工作。另外有几个稍微好一点的选择:三位小学教师、一位住在萨佛旁边的老小姐。最后终于挖到宝了!他们在一封来自罕皮拉的信件中找到一位真正的专业人士,一位叫做库卡·玛丽雅的女士,她原本是一名在凯米拉从事进出口贸易的秘书,现已退休。另外一位适合的人选是在托亚拉一处成人职业训练机构担任副主任的女士,名字叫做蒲萨丽,今年三十五岁,同时也教授商业书信课程。这两位女士都对生活感到失意,并且认真地考虑要寻短见。因为信任这则启事,她们还各自附上了详细的住址以及电话号码,希望能够派上用场。
尽管天色已经不早,但鉴于情况紧急,两位男士决定立刻和女士们开始联系。他们首先致电罕皮拉,但是没有人接听电话。
“也许她在这期间已经自杀了。”雷罗南推敲着。
他们接着打去托亚拉,蒲萨丽副主任也不在家,但是她在语音录音机里录制的讯息却请来电者留下留言。坎裴南上校于是自我介绍,并且简短说明致电用意,也为自己在将近午夜这么不寻常的时间里来电打扰而致歉。他表示自己会和同伴亲自前去拜访副主任,以便商讨一件重要的大事。
坎裴南和雷罗南决定立刻动身去托亚拉。晚间时,他们陆续喝了些酒,因此开车似乎有点危险。但他们最终明白,其实他们就算酒后驾车也算不上有什么危险,顶多就是送命。不啰嗦了,上路吧!上校负责开车,雷罗南总裁又高声朗读了一遍蒲萨丽副主任的来信。
我已经来到了人生的十字路口。我的心理健康状态相当糟糕。我小时候十分快乐,而且一直十分开朗而乐观,但是这几年在托亚拉的生活已经把我完全变成了另外一个人。我不再有自信。各种关于我的流言飞语在这座小镇四处散播。我在十年前离了婚,这没什么好奇怪,就算是在这里也不例外。但是在这次婚姻经历之后,我已经不想(或者说无法)再有伴侣,至少不想再有固定的伴侣。或许是我过于偏执,但我老是觉得这几年来一直有人在跟踪我,而且记录下我的一举一动。我觉得自己好像是这个小区里的囚犯。即便是我从前热爱的教学活动现在也都变得让我感到痛苦。
我已经让自己变成一个与世隔绝的隐士。我无法和任何人交谈,而且无时无刻不在提防着别人,我自己觉得这也不是没有道理。别人都认为我是个非常注重感官享受的女人,从某种角度来说,这也许是真的。我生性豪放,而且从来不拒绝别人的友谊。但我最终明白世界上没有一个人,或者说没有一个托亚拉的居民能够同等真诚地对待我。我真的再也受不了了。我只想要沉睡,永永远远地沉睡。希望我的这些秘密能够严格保密,倘若有别人知道了这些秘密,我的处境就会变得更加糟糕。我将不得不亲手结束自己的生命。
两位男士在海梅的夜幕中静静地开着车前进。过了一会儿,雷罗南总裁突然灵光乍现,想到在这么晚的时间里去拜访蒲萨丽副主任,应该要带个小礼物或是一束花,才不会显得有失礼数。上校也同意这个想法,但是他觉得在这么晚的时间要买到一束花恐怕有困难,因为所有的商店都打烊了。雷罗南盘算了一下,然后提议到路边去摘些野花,这时候正是野花绽放的季节。路经一个茂盛的小树林时,他要上校停下车,除了摘花,他还想利用这个机会去方便一下。
雷罗南总裁隐没在树林的阴影里。上校则在汽车旁边一边等着他,一边抽着香烟。这该死的摘花行动开始让他感到有些不耐烦。他大声叫着,要总裁回来。但后者在树丛后方某处,用醉醺醺的声音回应说已经找到花丛。反正至少是有些绿叶。雷罗南似乎是沿着马路平行前行的。于是上校便上车缓速推进。大约行进了五百公尺,他看见了站在人行道上的雷罗南,这位生意人一只手上拿着一束柳叶菜和一些其他连根拔起的林间野花,而另一只手上则拎着一只铁笼。上校在伙伴身旁停下,看到笼内有着一只正在发出威胁的叫声、不断喘息的狸猫。雷罗南非常激动,他说自己在树林里面走了很久,摘野花时意外地发现了这个铁笼陷阱。这只误闯陷阱的小动物开始尖声叫喊时,他真是担心这小家伙的生命。这是一只狸猫,如假包换的狸猫。倘若上校同意的话,他们可以把这只小家伙送给蒲萨丽。坎裴南可不觉得一只袋类野生动物是送给自杀候选人的好礼物。他请求雷罗南把小动物和笼子拎回原处。
这位失望的生意人只好走回树林里。但他很快又折返回来,说他找不到原来的地方了。上校建议他随便放在某个他中意的地方,但是被雷罗南拒绝了。没有人能够保证设陷阱的猎人能够找到被移位的铁笼。这只小动物会一直被关着受苦,直到最后饥渴交迫而死。
因为不能让笼子里的小家伙听天由命,上校只好让步。
雷罗南也不想就地放归这只狸猫,因为它随时可能兽性大发,并且对附近的雏鸟或野鸭造成威胁。他将铁笼放到汽车的后备箱里,然后捧着花束坐到上校身旁的前座上。
坎裴南不太高兴,他的同伴根本是喝醉了,而且一直在自找麻烦。接下来,他们一路上都保持着沉默。
将近凌晨三点时,雷罗南总裁和坎裴南上校按响了副主任家的门铃,她住在托亚拉市中心一栋公寓的三楼。门开了,他们获允人内,总裁带着狸猫和从树林采来的新鲜花束。
……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