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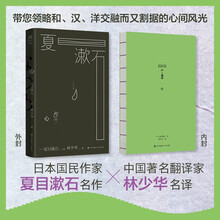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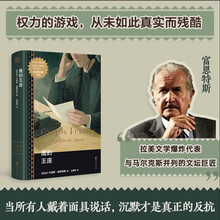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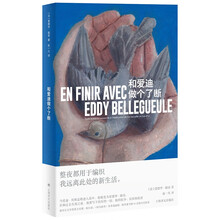
“我很乐意,”他又说,“年度报告的工作可以委任给别人,给那些更加有才能的同事。比如我很乐意把位置让给尊敬的天主教长老,如果当初他没有在第一天就推辞这个荣誉的话。难道我们真的能够想象,这位年迈斗士的自愿退让换来的是拉诺丁的上台吗?”他的眼神透露出一种真正的伤心,一种肉体痛苦的焦虑,仿佛这个不幸的人徒劳地试着表达他的仇恨。
“我对拉诺丁先生没有任何成见,”那个缓慢低沉的优美嗓音又说,“我甚至很看重他。从他的批评,甚至是不公正的批评中,我总是能汲取益处,啊,我的朋友,空谈派的人的优点在于:他们恰恰能够唤醒我们身上的才能,这些才能有时会被我们平庸的生活磨损削弱。他们给我们提供了非常有用的帮助。“然后塞纳波开始笑了,笑容显得很沉重。
“我崇拜您,”佩尔尼松充满感情地喊道,“您在这虚无的喧闹声中保持着清醒,不管是在圣坛还是在教会的其他地方。拉诺丁先生的立场,他的固执会损害令人敬重的大人们的利益,您即使好心也不能忘了这一点,‘我们将付出代价,一次又一次,昨天,您尊贵的朋友西弥尔大人在我面前说。
’他将会给我们好看的,或者我们可以这样解决:只要几个没有授权的狂热选民带着一小撮无知的人表示正式反对,不,名义上的反对就可以了。这个要求过分吗?”汗水终于顺着这个矮小男人的额头流了下来,他似乎在经历极大的痛苦。佩尔尼松在一家激进党人的报纸上编辑宗教专栏,由一位保守的金融家出资赞助,为社会党人说话。佩尔尼松把身心都投入这混杂了三方面力量的事业中,用尽了他的廉耻、耐心和昆虫一般的技巧。
《新晨曦》办公室人员几乎不认识他,他是没有书本的作家,没有报纸的记者,没有教区的高级教士,生活在教堂、政治、世俗和学术协会的边缘处。但是佩尔尼松劳损的,不吉利而且有点驼的背影对那些人来说再熟悉不过,而且他急于出售自己,别人并不是那么需要。
急切地想出卖往往会导致掉价,最后就会像熟透且没用的食物一样都烂在屋子里。他是德尚圣母神学院的学生,一直到毕业的最后一天对他的使命还一知半解,接着他勉强过了会考之后就长时间的失去了踪影,直到现在体现他重要性的时刻才出现。他每个星期得在教区公报上留名,而且还要在雅各布街的一家小料理店编辑《罗马信札》,除了他还有别人能扮演这么阴暗的角色吗?但是他像他祖先奥弗涅人一样懂得一点一点地储存名声.他的先祖在夏天用他们的汗水浇灌贫瘠的土地,冬天就去巴黎卖连猪都不吃的栗子,一生都辛勤劳作,梦想积累财富吃饱穿暖,直到临终医生来临前,才匆忙的变得体面干净。
这些《罗马信札》也不是毫无价值,它们至少还有对抗另外一些信件的价值,那些信件也是希望泄愤的失意人以同样心情和头脑写出来的。
那些信件可能是由不同的作者写的,但是同样的晦涩难懂,同样充满仇恨和贪欲,信件的写作手法很温和,针砭所有教会中所有体面的人。
佩尔尼松怀着尊敬的心情观察了一会教士,满脸皱纹的微笑着说:“我不愿让您生气。然而教廷大使昨天说……”“不要谈论教廷大使。”塞纳波几乎是祈求似的说道。“教皇的热情终于转变成对我们共和国部长们的愤怒,民主就是喜欢排场:一大堆诡计多端的教士被送过来,又无耻,又恶心,这一个。我敢发誓还听不懂希腊语,于贝尔议员。”他抚摩着脸颊,发了一阵呆,又温和地说:“不过,无所谓,您也听不懂。”“您忘了,”佩尔尼松压抑住快乐喊道(虚荣的人,即使不经意的被刺激了一下,也会有很灵敏的反应),“您忘了我在1903年巴黎的神学院拿过希腊语的翻译奖,啊,我多想从事文学,但是总有做不完的琐事。”“达戈曾说过:平静的秘密就是不要期待任何幸福的事。特蕾莎圣女在他之前也写过:某些会面是简单的,甚至是苦涩的……”塞纳波回应道。
他的手焦躁地敲打着路易十六办公桌的红呢布。时钟敲响了十一声。
“我担心您会疲倦,”佩尔尼松说,“我知道您很少熬夜.拜访您,让我远离喧闹的巴黎,让我如此受益,每次离开您的时候,我总是充满了信心和信仰。您对人和事的看法是如此平静,您有智谋又很宽容!我以您为荣(允许我重复,我尊贵的大人),您不仅是整个世界的保护者,也是我可怜灵魂的导师。”塞纳波神甫看着摆钟,坐在椅子上半闭着眼睛,尽力使他的右手不发出声音,他发出简单而又威严的话语:“我欣赏您的耐心和顺从,而且有时我对您的责备和警告很严厉。但是每周见您一次并非我所愿,您知道部里有很多事情,加上编辑史学花费了我很多的时间,您是个虔诚的青年,我不是推卸责任,如果我的建议对签有用,我是不会拒绝您的。但是我还是希望您去找其他的教士。您的选择很多,我知道您认识不少人才。如果您不想对某个平凡的神甫吐露心声的话,那么今天是我最后一次听您的祷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