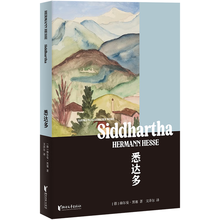油漆的桌面上,尘埃留下了各种小东西的痕迹。这些东西曾经有一段时间留在桌子上——有几小时,几分钟,或者几星期——然后被拿走,而它们的底部,由于灰尘的作用,在桌上留下了清晰的印记,有圆形,有方形,有长方形,也有其他更复杂的形状。这些印记有的部分重叠在一起,有些已经模糊不清,或者被抹布之类的东西擦去了一半。
这些印记中有的轮廓十分清晰,可以正确地看出形状,也就不难在附近找到留下这印记的物件。那圆形的显然是玻璃烟灰缸,它就在边上摆着。桌子左下角的方形印记与那铜台灯的底座显然是吻合的。那台灯现在的位置是在桌子的右角:一个方形的底座,大约二公分厚,上面有一个同样厚度的圆盘,圆盘的正中间是带有凹槽纹饰的灯柱。
灯罩在天花板上投射出一个圆形的光圈。但这个光圈是不完整的:其中有一部分在天花板的边缘被切断,延伸到桌子后面的那堵墙面上。这堵墙与其他三面盖满壁纸的墙不同,从上到下,在其宽度的大部分地方,被红色的厚窗帘遮盖起来,窗帘布是厚实的天鹅绒。
外面正在下雪。人行道深色的沥青路面上,风正在驱赶着晶体状的干雪。每阵狂风过后,雪花又重新飘落下来,形成白色的线条,平行的、交叉的、螺旋形的线条,然后又立即被风吹散,重新卷入拔地而起的旋风中,接着又重新凝结,形成新的螺旋、漩涡、波纹、曲线,然后又立即分散、解体。行人们把头垂得更低,用手更紧地护住眼睛,只能看到脚前的几公分地面,几公分灰白色的路面,两只脚一前一后交替出现,交替向后退去。
钉上鞋钉的后跟在沥青路面上发出断断续续的响声,沿着笔直的马路,有规律地靠近,在严寒肃杀的夜空中显得越发清晰可闻。但鞋跟的响声传不到这里,外面的任何声音都传不进来。马路太长,窗帘太厚,房子太高。任何噪声,哪怕是减低了的声音,都无法穿透这房子的墙壁,没有任何震动,也没有任何气流能穿越过来。在寂静中,细微的尘埃颗粒在慢慢降落,在台灯的灯光中几乎看不见这些尘埃,它们慢慢地垂直地下降,永远保持相同的速度,于是灰色的细尘形成均匀的一层,停留在地板上、床罩上、家具上。
打蜡地板上,毡底便鞋踏出几条发亮的通道,从床到衣柜,从衣柜到壁炉,再从壁炉到桌子。桌子上,东西的移动破坏了尘埃颗粒的均衡,尘埃的厚薄取决于桌面被覆盖时间的长短。桌面上的有些地方,灰尘突然中断:清晰的、像用直线笔画出的,是位于桌子左下角的一个正方形,这个方块并不在桌子的顶角处,而是位于离桌边十公分左右的平行线上。这个方块每边的长度大约十五公分。方块中间的桌面,呈红褐色,闪闪发亮,几乎没有任何灰尘在上面。
桌面的右边,有一个模糊的形状,上面已经覆盖着好几天的灰尘,但还是露出下面的桌面颜色。这形状的一角,四周的轮廓还比较清楚,这是一个类似十字架的东西:身体是长的,大约有餐桌刀那么大小,但比餐刀更宽一点,一头是尖的,另一头微微隆起,中间被一条短的横杆从垂直的方向穿过,横杆由两个火焰状的延伸物组成,对称地位于竖杆的两侧,横杆与之交叉的地方是在隆起一端的根部,也就是在竖杆三分之一的地方。你也可以说这是一朵花,隆起的一端是长长的关闭的花冠,下面是两片横向的小小叶瓣;或者你可以把这看成是一个人物的图案,椭圆形的头部,两只短短的手臂,身体的末端是尖尖的脚;也可以说这是一把匕首,上面是刀把,中间是护手,下面是两边带刀带刃的刀身。
再往右,沿着花的尾巴或者刀梢所指的方向,是一个圆圈,稍稍有些模糊,周围的一边被同样大小的第二个圆圈盖住。这第二个圆圈是完整的,产生它的东西就在桌上:玻璃烟缸。接着是一些不清晰的、相互交叉的线条,显然是各种纸张造成的痕迹。因为不断移动,所以痕迹已经弄乱。有些地方图案清晰,有些地方被灰尘盖住,还有的地方像被抹布抹去了一半。
桌子的右上角,立着那只台灯:十五公分见方的底座,底座上是同样直径的一个圆盘,凹槽花纹的灯柱上是一个深色的略呈圆锥形的灯罩。灯罩的圆顶上有一只苍蝇正在慢慢地不停地移动。灯光在天花板上投射出一个变了形的影子,你无法辨认出那昆虫身体上的各个部位:没有翅膀,没有身体,没有腿。整个苍蝇变成一根极细小的线条,断断续续的、不封闭的线条,像缺了一只角的六角形,这是电灯泡里面红色灯丝的形象。这缺角的六角形的一角正好碰到电灯所产生的大圆形灯光的内边。苍蝇慢慢地在上面移动,沿着灯光的圆周不断地移动。当它移动到垂直墙面的时候,就消失在厚实的红色窗帘里边。
外面正在下雪。外面曾经下过雪,下着雪,外面现在还在下雪。密密的雪片柔和地飘落,均匀地、不停顿地、垂直地飘落——因为没有一丝风——在高高的大楼正面的灰色墙前。紧密的雪花叫人看不清屋顶的布局和线条,也看不清窗洞的情况。估计这些窗洞的形状每一排都一样,而且每个楼层的窗,甚至这条笔直的马路从头至尾的大楼上所有的窗都完全一样。
右边拐角处,另一条相同的马路交叉而过:这是一条同样没有车辆的马路,同样高高的灰色大楼,同样紧闭的窗户,同样杳无人迹的人行道。人行道一角,亮着一盏煤气街灯,尽管现在正是大白天。但这是一个没有光彩的白天,它使所有的东西都变得平坦而黯然无光。这一排排房子在大雪中并没有产生美丽的景观,只是毫无意义的一大堆线条的纵横交错。不断降落的大雪使这里的景观变得毫无生气。这糟糕的景色像是在一堵光秃秃的墙面上乱涂出来的伪造的图画。
在天花板与墙的交界处,那只苍蝇的影子,也就是电灯丝放大的图像,重新出现,并在强烈的灯光产生的光圈边缘继续它的行程。它的移动速度始终是缓慢而持续的。在光圈左边的黑暗区域中,冒出一个亮点,有点像深色羊皮纸灯罩上一个小小的圆孔透出来的光影,确切地说这不是一个点,而是一条开口的断开的细线,一个缺了角的规则的六边形:来自同一光源即同一根红色灯丝产生的放大了的新形象,这一次却是固定不动的图像。
还是那根同样的灯丝,一只同样的灯,或者略大一些的一只灯,在两条马路的交叉口发出无用的光。灯泡装在玻璃灯箱里面,底下的灯柱是铸铁的,式样陈旧,装饰过时的煤气灯变成了电灯。
铸铁灯柱的底部是一个锥形的基座,上窄下宽,底座上围绕着几个大小不一的圆环,四周环绕着浮雕状的常春藤树枝:弯曲的茎,掌状的叶,尖尖的叶子有五片,脉络清晰,叶面上涂的黑漆已经部分剥落,露出里面的铁锈。再往上是一个人的一段腰,一只胳膊,一只肩膀,斜靠在街灯柱上。这个人穿一件说不清颜色的军大衣,已经褪色,像绿色或者接近卡其布的颜色。他脸色发灰,面容消瘦,使人感到他已极度疲劳;但也可能是几天没刮胡子更使人产生这种印象。长时间的等待,特别是长时间伫立在寒风中,使他的脸颊、额头和嘴唇变得毫无血色。
跟他脸上的其他部位一样,他的眼睑也是灰色的。这个人双眼低垂,头向前倾斜,目光朝着地面,就是说看着街灯脚前的积雪的人行道边缘。他穿一双圆头大皮靴,粗糙的皮面上满是擦伤和碰坏的痕迹,但还看得出黑色的鞋油印。地面的雪积得并不厚,所以那双皮鞋还没有隐进雪里,鞋底是处于——或基本上处于白雪的上面。人行道边缘的积雪没有任何践踏的痕迹。那里的雪没有光泽,但洁白、均匀,雪面上保持着细散松软的颗粒状态。街灯柱底座最后一个突出的圆环上部已经有少许积雪,在街灯的黑色圆环底座上形成了一个白圈。再往上,白白的雪亦停留在街灯底座的其他突出部位上,白色线条勾画出一个个圆环以及常春藤的树叶、树枝、叶脉等横向或倾斜的部位。
由于几次变换站立的地方,军大衣的下摆扫去了脚下的小片积雪,再加上那双皮鞋的移动,很快在双脚周围堆起了积雪。积雪上出现黄色的斑点、从底部翻起的积雪硬块,以及鞋钉踩出的梅花形的深深脚印。衣柜前的那片地板上,毡底便鞋踩出一大块光亮的区域,还有一块是在桌子前面,那地方应该是放置办公椅、椅子、圆凳或者某种座位的地方。从衣柜到桌子,便鞋在地板上留下了一条光亮的狭窄通道;第二条通道是从桌子到床边。外面,沿着与房子的墙相平行的方向,在墙与马路上的排水沟之间,更靠近墙的地方,有一条笔直的路出现在积雪的人行道上。那是由走过的行人(目前已经消失)踩踏出来的,上面的积雪已经变成灰黄色。
……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