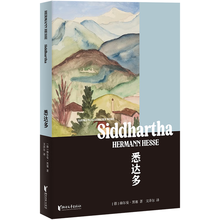第一幕
自称亨利·罗宾的人早早就醒来了。他花了好一阵时间才算弄明白,自己是在什么地方,呆了多久了,在这里都干了些什么。他没有睡好,和衣躺在临时铺褥上,在这个资产阶级尺度(但现在却既没有床,又冷如冰窟)的房间中,当年,克尔凯郭尔两度居留柏林期间,就曾把这种房间称作“尽头房间”,他第一次居留是在1841年冬天,与蕾吉娜·奥尔森分手之后的流亡①,另一次是1843年春天,对柏林满怀希望的“重归”。亨利·罗宾只觉得关节僵硬,浑身不自在,简直起不了床。他咬牙挺身,终于完成了起床任务,解开扣子,活动了一下身子,却并没有脱下那件又硬又皱的大衣。他一直走到窗户(窗朝向猎手街,而不是朝向宪兵广场)跟前,拉开了破烂不堪的窗帘,小心地没有把它撕烂。看样子,曙光才刚刚初露,在眼下季节的柏林,这表示时间应该是七点多一点。但是,这天早上,灰色的天空是那么低矮,人们甚至不敢确信无疑地承认这一点:时间很可能还要更晚一些。HR打算对一下表,他整夜都戴在手腕上的那块表,却发现它已经停了……这没有什么奇怪,因为他昨天晚上忘了给它上弦了。
他回到了桌子前,那里现在比刚才更明亮了一些,他立刻明白到,在他睡觉期间,这套房子里有人来过:抽屉大开着,里面空空如也。夜用望远镜不见了,精巧的手枪不见了,身份证不见了,带一个血洞的硬皮夹子也不见了。还有,在桌子上,两端都写满了他纤细字迹的那张纸同样也不翼而飞。在它的位置上,他看到一张一模一样的白纸,普通的公务尺寸,上面匆匆地涂写着两句话,字体很大,倾斜着,横跨整张纸:“干了的已经干了。但,在此条件下,你最好也消失,至少也要消失一段时间。”署名很清楚,“斯泰恩”(词尾带一个e),这是皮埃尔·加兰使用的代号之一。
他是怎么进来的?HR记得清清楚楚,在跟那个可怖的老太婆见过令人担忧的一面后,自己明明是用钥匙锁了门的,随后还把钥匙放在了抽屉里。但是,现在,他把抽屉拉到了头,却发现根本就没有钥匙。他心中顿生不安,担心(毫无来由)自己被反锁囚禁起来,便走向写有“J.K.”的小门。它不仅没有用钥匙锁着,而且连关都没有关上:门扇只是简单地搁在槽内,只有几毫米,无论是平头锁舌,还是斜面锁舌,都没有啮合在锁槽中。至于钥匙,它也没有留在锁眼上。剩下了一种解释:皮埃尔·加兰还有另一把钥匙,他用它开了门,进了套间;出门时,他带走了两把钥匙。但,出于什么目的呢?
这时,HR感到一阵头疼,潜在的,隐隐约约的,从他醒来后就越来越显得明确,妨碍着他的推理或假设。实际上,他感到自己比昨天晚上更迟钝,仿佛从水龙头喝的水里含有某种毒药。假如那是一种安眠药的话,他就有可能连续不间断地睡了二十四小时还多,只是这里没有任何办法能证明它真实与否。当然,在自来水中下毒不是一件容易事;那需要有某种非公用的供水系统,要有一个私有的蓄水池(这也许能解释为什么水压那么不足)。想着想着,他觉得有一点尤其令人费解,在一片被遗弃给流浪者和耗子(同样也给了杀人凶手)的街区里,在这个被部分摧毁的楼房中,城市的自来水系统居然修复了。
无论如何,这样一个令人疑惑、与经验不符的事实,即一个夜间窃贼没能把一个熟睡的人弄醒,恐怕只有一次人为催眠的熟睡,能让它更说得通一点。这个当时的熟睡者,希望将自己昏昏沉沉、迷迷糊糊、跟浑身关节一样绵绵无力的头脑,恢复到一种正常状态中来,便走进卫生间,想用冷水洗一把脸。不幸的是,这天早上,水龙头拧到了头,都不见有一滴水流出。整个的管道看起来很久以来就一直是空空荡荡的。
阿灰,中心的同事们都这样叫他的外号,发音是阿歇尔,跟塞纳一瓦兹省那个小城镇的名称一样,他所属的那个秘密小分队就驻扎在那里,阿灰(在德语中,它的意思是灰尘颜色的男人)重又抬起脸,对着洗脸池上方有裂缝的镜子。他简直认不出自己来了:他的面容模糊一团,头发乱蓬蓬的,假胡子也挪了位置;它的右侧扬了上去,微微有些斜。他不打算把它再贴一次,决定干脆把它撕下来。无论如何,它看起来倒是更为滑稽,而不是有效。接着,他又照了照镜子,惊讶于这样一张无名的脸孔,尽管它比平常更加不对称了,但却还是毫无特点。他迟疑地、不知所措地走了几步,这时,想起来该证实一下帆布旅行包中的内容,便把包彻底掏了个空,把里面的东西一件一件地放到他睡过觉的那个不太友好的房间的桌子上。似乎没有少什么东西,物件的摆放还是老样子,处于他当时仔细码放时的确切位置。作假的双层底看来没有打开过,因为夹层内细小的记号没有被触动,他的另两本护照始终躺在那里。他漫无目的地把它们乱翻一气。一本上的姓名是弗兰克·马修,另一本上是鲍里斯·瓦隆。两张照片上都没有留胡子,假胡子没有,真胡子也没有。那个所谓的瓦隆的脸,也许更像是撕了胡子后出现在镜子前的脸。于是,阿灰拿起这个所有必要的签证全都一样的新证件,把它放进上衣内侧口袋,又从口袋中掏出亨利·罗宾的护照,插入帆布包夹层中弗兰克·马修的边上。然后,他又将所有物件放回原先的位置,还把皮埃尔·加兰留在桌上的那张纸条也添了进去。
“干了的已经干了……你最好也消失……”
阿灰还利用这一时机,从洗漱包里拿出他的梳子,不等转身面向镜子,就匆匆拢了拢头发,不过他避免梳得过分光滑,不然就不怎么像鲍里斯·瓦隆照片上的样子了。在朝周围环顾了一眼,仿佛担心忘了什么之后,他走出了套间,把门仔细地掩成皮埃尔·加兰当时留下的样子,让门扇留出约五毫米的缝隙。
就在这时候,他听到了对面套间中传出的声音,这提醒了他去问一问那个老太婆,楼房里是不是有自来水。他为什么要害怕呢?但是,正当他准备敲响木板门时,一阵破口大骂突然从屋子里爆出来,那是一种不太像柏林口音的喉音很重的德语,然而,他还是注意到,“杀人犯”一词重复了好几遍,而且喊得越来越响。阿灰抓住他旅行包的皮拎带,一把将他那个沉重的帆布包拎起,急急忙忙地但却小心翼翼地下楼,像夜里上楼时一样地扶着栏杆,一级一级地走下楼梯。
他现在把皮拎带搁在了左肩上,也许是行李太重的缘故,腓特烈街似乎比他想象的要长得多。废墟堆中依然矗立着的很少几幢楼房,尽管百孔千疮,却披挂上了种种临时性的修复,当然啦,它们中既无咖啡馆,也没有旅店,能为他提供某种慰藉,哪怕是喝上一杯水。此外,也没有发现任何卖东西的店铺,相反,东一处西一处的倒是不时出现一些铁皮门窗板,恐怕好几年都没打开了。整条长长的街上,一路上没有半个人影,连几条横马路上也没有碰到人,到处是一片片荒芜的瓦砾场。然而,一些破残的楼房经过了马马虎虎的修补,里面无疑住了人,因为可以辨认出,窗户后站着一些一动不动的人,正透过多少修整过的肮脏的玻璃窗,观察着下面这个奇怪的旅行者,这孤旅者细长的身影前进在没有车辆的马路中央,在一道道墙面和一堆堆灰泥之间,一个黑色帆布包,异常厚重和僵硬,挂在他肩上,拍打着他的胯骨,迫使这人在不恰当的重荷下弯下了腰。
阿灰终于来到了岗哨前,离那标志着边境的可憎的铁丝网挡板只有十米。他出示了有鲍里斯·瓦隆姓名的护照,德国哨兵见他走近,便从哨所中出来,仔细地查看上面的照片,然后又查看了民主共和国的签证,最后,是联邦共和国的签证。穿军装的那人,特别像最近那次战争中的一个占领者,他用一种审讯者的口气指出,印戳符合规定,但却有一个基本细节上的毛病:缺少进入民主德国领土时的入境章。旅行者也瞧了瞧有问题的那一页,假装在寻找那个哪怕出现奇迹都不会显现的印戳,接着解释说,他是从巴特爱斯费尔德一爱森纳赫公路走廊入境的(这一说法有部分是确切的),最后偶然碰上了一个图林根的军人,也许是仓促匆忙,也许是没有经验,忘了在过关时盖戳了,很可能他是忘记了,也可能当时没有印泥了……阿灰滔滔不绝地说着,用的是一种不怎么确切的语言,不知道另一位是否明白其中的曲折,这在他看来并不重要。关键难道不是要显得镇定自若,轻松自然,满不在乎吗?
“KeinEintritt,keinAustritt!”①哨兵说得很干脆,固执而又合乎逻辑。于是,鲍里斯·瓦隆在他的几个内袋中乱摸一气,仿佛在寻找着另一个证件。士兵凑近来,表现出某种兴趣,瓦隆费劲地猜测着他的意思。他从他衣兜里掏出来并打开的,是他的钱包。另一位当即看出,里面的钞票是西德马克。一丝狡猾而又贪得无厌的微笑顿时把他那张一直阴沉沉的脸映得发亮。“Zweihundert”②,他简明地宣布说。二百德国马克,这有点太贵了,只能换几个多少读不太清楚的字母和数字,在塞在帆布包夹层中的亨利·罗宾那个证件中,他见到过那些数与字。但是,眼下没有别的办法。于是,假旅行者再一次把护照递给热心的检查者,当然,在此之前,不加掩饰地在里头塞进了两张指定数额的大票。士兵立即消失在了警方办公室中,一个歪歪扭扭地坐落在废墟中央的预制箱子中。
……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