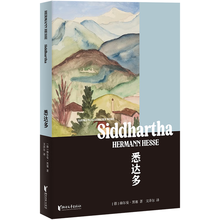一越过一直挡着我们视线的那一排岩石,我们就又看见了坚实的陆地,长着松树的山岭,两座白色的小房子,还有那条坡度不大的道路的尽头,我们就是在那里上岸的。我们已经在岛上转了一圈。
然而,如果说,我们毫不费力地就认出了陆地一边的景色,那么,对那条把我们跟陆地分隔开的狭窄的海峡,却不是如此,特别是对我们曾待过的海岸,就更不是这样了。因此,我们不得不花上好几分钟,才终于确信无疑,通道被切断了。
我们本应该一眼就看出来的。从半山腰开挖出的公路,跟海岸平行地延伸下来,到沙滩的高度时,以一个突然向右的拐弯,跟某一个石头堤坝相衔接,堤坝相当宽,足以通一辆汽车,在低潮时,它能让人步行通过海峡而不湿脚。在拐弯处,有一面由一堵矮墙支撑的高高的斜坡,公路就是在那里接合上的;从我们现在脚踏着的地点看去,它遮挡住了堤坝的顶端。堤坝的其余部分淹没在海水中。仅仅是由于视角的改变,我们有一阵子困惑:这一回,我们是在岛上,而且从相反的方向到达,朝北而行,而路的尽头却是向着南面。
在我们面前,就是那条公路,它从海岸的坡顶,就是在以三四棵远离小树林的松树为标志的拐弯角后面,一路延伸下来,一直到堤坝,右手边是海峡,还有海岛,它现在还不完全是个岛。海水平静得如池塘中的水,几乎快漫到石头堤岸的上面,平滑的褐色堤面显现出跟周围的岩礁同样被浸蚀的面貌。满是苔藓的细小海藻,被太阳晒得颜色褪了一半,给堤面染上了绿茵茵的斑点——这是长期频繁浸泡的证明。堤坝的另一头,同这一边一样,堤面难以觉察地微微鼓起,跟穿越了小岛的土路相连接;但是,在这边的岸上,道路随之又完全平坦起来,与堤坝一起构成一个很开的角。尽管没有什么斜坡证明此角的存在,一堵矮墙——与此角相对称——依然保护着通道的左侧,从上坡的开端,一直到沙滩的上侧界线——在那里,大小不等的鹅卵石让位于荆棘丛。岛上的植物比起围绕着我们的那些已然灰蓬蓬、黄兮兮的植物来,似乎还要更干枯些。
我们沿着山腰的公路,朝堤坝方向往下走。两座渔民的小房子紧靠着路的左侧;小屋的正面新涂了灰泥,并用白灰刷得雪白;只有围住门窗——一道低矮的门,一扇方形的小小窗子——的大块石头露在表面。窗子和门都关着,窗玻璃被漆成亮蓝色的木头护窗板遮挡住。
再往下,在从小山岭的土壤中开凿出的公路旁边,露出一堵黄色的黏土墙,垂直的,一人来高,上面布满了一片一片的裂缝,里头刺棱出尖利的鱼刺;荆棘和山楂树构成一道高矮不齐的篱笆,圈住整个建筑,挡住了投向荒野和松树林的视线。在我们的右边,则相反,公路边只有一面狭窄的斜坡,高仅一两个台阶,目光放去,可以直达海滩的岩石、海峡中平静不动的水、石头砌的堤坝和小岛。
海水几乎涨到了堤面上。我们必须赶快行动。再迈几大步,我们就走完下坡路了。
堤坝跟公路形成一个直角;公路的尽头紧靠着一面黄土的墙,三角形的,标志着开在半山腰的斜槽的结束;它的底部由一道矮墙保护着,矮墙顺着石头的堤面向右延伸,明显越过了三角形的尖角,在那里仿佛构成了一段护墙。但是,它在几米之外就中断了,而同时,斜坡坡度也减缓,最后与堤坝的中间部分——水平的,被海水冲得很平滑——会合在一起。
到了那里后,我们便犹豫起来,不知该不该继续走下去。我们望着面前的海岛,想估算一下,在那里绕一圈的话要费多少时间。当然,有一条土路穿越海岛,但那样走的话实在不太值得。我们望着面前的海岛,在我们的脚下,通道的石头颜色发褐,十分光滑,有的地方还覆盖着绿色的半干的海藻。海水几乎涨到了与它们齐平的位置上。它平静得如同池塘中的水。人们看不到它上涨;然而,人们却感觉到它在上涨,因为,水面上的灰尘线,在一丛丛的海藻之间慢慢地移动着。
——我们再也回不来了。弗兰兹说。
从近处贴着水面望去,海岛似乎比刚才高多了——也宽多了。我们重又望着灰色的小线条,它们以一种规则的缓慢速度向前推进,在露出水面的墨角藻之间卷成旋涡。勒格朗说:
——它不会涨得那么快的。
——那么,我们赶紧吧。
我们匆匆地出发了。但是,刚刚穿过海峡,我们就离开了堤面,从右面下到了环绕着小岛的海滩上,继续沿海岸线走着;那里,有一块不平整的土地,布满了岩礁和孔洞,走起来十分困难——比我们预想的要慢多了。一旦走上了这条道路,我们就不想再返回。然而,我们越往前,岩礁就越多,越大。好几次,我们不得不攀越真正的岩坝,它们远远地深入到海里,想绕都绕不过去。在别处,我们还得穿越一些虽相对平坦,但石头上却布满了滑溜溜的藻类的地带,这又使我们耽误了更多的时间。弗兰兹又重复了一遍,说我们再也不能回头穿过这水面了。实际上,我们根本不可能弄清楚潮水上涨的速度,因为,我们没有时间停下来察看。现在也许是平潮。
同样很难知道,我们已经走过了路程的哪些部分,因为,一个个的海岬总是屹立在我们的眼前,海岸的凹湾一个接一个地出现,而不给我们提供丝毫的坐标。此外,不要在如此别扭的地方耽误每一分钟的担心,缠住了我们的注意力——于是,风景消失了,让位于某些威胁性的片段:一个要避开的水坑,一系列会晃动的石头,一大团里头不知道藏着什么的海藻,一块要攀越的礁石,另一个洼坑,边上堆着黏黏糊糊的藻类,还有颜色像淤泥一样的沙子,一脚踩上去,便会深深地塌陷——好像要把脚拉住似的。
终于,在穿越了很长时间以来就一直挡着我们视线的最后一排礁石后,我们重又见到了坚实的陆地,长着松树的山岭,两座白色的小房子,坡度很缓的公路尽头,我们就是从那里上来的。
我们没有立即弄清楚堤坝在哪里。在海边的高坡和我们之间,只有一条海峡,那里的海水流得很急,朝我们右方汹涌而去,在好几处形成激流和旋涡。海岛的滩岸本身看来也变了:眼下,它是一个黑糊糊的沙滩,其表面显得十分平坦,无数个水洼在闪闪发亮,顶多只有几厘米深。一条小船停泊在一条很短的木头防波堤旁边。
从这个地方通向海滩的小径,并不像我们还留有记忆的那条土路。先前,我们并没有注意到任何船只的存在。至于用作停泊码头的防波堤,它跟我们来的时候借道的那条堤坝,没有任何的共同点。
我们不得不花了好几分钟时间才发现,在前方三十米处,有两道矮墙,它们在通道的两端构成了护墙的接口。堤面在它们之间消失了。海水在那里汹涌奔流,泛起乳白色的泡沫。堤坝高起的两端自然露出在水面上,但是那两道小墙足以把它们遮挡。人们同样也看不到公路的低处,它在斜坡的后面拐了一个直角的弯,连接到了堤面的石头上。我们又一次望着灰色的灰尘线,它们在一丛丛的海藻之间有规则地慢慢地推进着,并旋转成旋涡。
除了水面上几乎发觉不了的这一运动,海水平静得如同池塘里的水。但是,水几乎已经涨上了堤坝的表面,而在另一端,它至少还差三十厘米。其实,在离海湾入口最近的死角中,海水上涨得还要更快。当堤坝对潮水的阻碍被冲破时,突然产生的水位差会产生一股水流,立即把通道切断。
——我们再也回不来了。弗兰兹说。
是弗兰兹第一个这样说的。
——我说过,我们再也回不来了。
没有一个人回答他。我们跨过了小小的防波堤;试图跳过矮墙来穿越堤坝是没有用的,这一点显而易见——并不是那里的水已经很深,而是因为波浪的力量会使我们失去平衡,在一瞬间里把我们卷走。从近处,可以清楚地看到水位差;在上面,海水平滑如镜,表面纹丝不动;接着,它突然从岸的一边向另一边卷曲成一根圆柱体似的棍子,几乎没有什么波浪,它的流动是那么有规律,尽管流速很快,却仍然给人一种静止的印象——一种在运动中的脆弱停息,就像快镜头提供的那些令人赞叹的形象:一粒将要打破一潭死水之宁静的小石子,被摄影术固定在它的坠落当中,离水面只有几厘米。
接着,只是开始出现了一系列的鼓凸、凹陷、旋涡,它们那白花花的颜色说明了其中的混乱。然而,那里同样,从一定程度上说,这是一种固定的混乱,浪尖和混沌不停地占据着相同的位置,保持着相同的形状,以至于人们可以相信,它们被冰冻得一动也不动了。总之,整个的这一股强力,跟在一团团海藻中间的小小灰线比起来,并没有一个如此不同的——更不用说更阴险的——面貌,我们又继续起刚才被沉默打断了好一阵子的谈话,试图驱驱邪:
——我们再也回不来了。
——它不会涨得那么快的。
——那么,我们赶紧吧。
——你们以为在另一边能发现什么?
——我们绕一圈,不要停下来,用不了多长时间的。
——我们再也回不来了。
——它不会涨得那么快的;我们有时间绕它一圈。
我们转过身来时,发现一个男人站在小船边上的小防波堤上。他朝我们这面眺望着——至少,几乎是朝我们这边望着,因为,他的神情更像是在观察着稍稍位于我们左边的、在浪沫中的某个东西。
……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