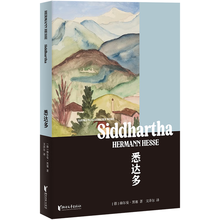我蹑手蹑脚地走进昏暗的房间。这间屋子非常女性化,充斥着印度织物,劳伦斯那浓郁厚重的香水味像往常一样漂浮其间。同样一如往常,这股味道令我头疼。劳伦斯在少女时代曾患过两三次皮肤过敏,从那以后她的母亲便劝她将百叶窗和玻璃窗关上睡觉。这样一来,香水味就更让人头疼了。
好在我刚才在浴室里打开了所有窗户,呼吸了五分钟巴黎城郊猛烈、清新的乡间空气,因此当我向着睡美人劳伦斯俯下身的时候,感觉还不错。她黑色的长发紧贴在古典的脸廓之上,这使她看上去很像罗马圣女,当年我就发现了这一点。她微微叹息。我更深地弯下腰,将嘴唇印在她的脖颈上。她有玫瑰色的肌肤和黑色的睫毛,尽管她总是为身材太瘦而苦恼,但依然神采焕发、美丽动人。我稍稍将毯子往下拉了拉,让她多露出来一些,但她似乎受到了冒犯,在毯子退到肩膀时按住了它。
“啊,求你了!别这样!才清晨……就有怪念头!真的!安静点儿!” 像许多女人一样,她总是犯点儿小错,例如在别人求欢时嫌恶地说: “你脑子里只想着这个!”或是问:“你不再爱我了吗?”可事实明摆着正相反。她耽于肉欲,但在谈论爱情时却不像个荡妇,反而如同上流社会的贵妇,天真而露骨。更何况,还有哪个女人会郑重其事地谈论爱情呢?就我所知,男人在这方面并没有做得更好些。
“确实,”我说,“我们吵架了。”“我并没有生你的气,我只是伤心。”“伤心?为什么?我做了什么?”我已经默认了落在头上的罪名。
的确,昨天晚饭的时候,我似乎跟一位银行家的年轻妻子说了几句暧昧的话,但我却怎么也找不出我和她的对话有什么弦外之音。
更何况她的银行家丈夫还是我岳父的挚友。我的岳父是个令人讨厌的家伙,七年前,他宣称我只是个小白脸,结婚仅仅是为了抢走他唯一的、无邪的、富有的女儿。
……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