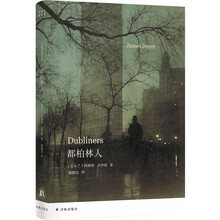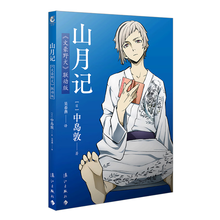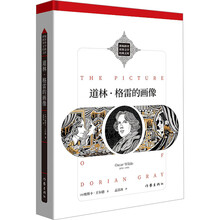阿兰·罗布-格里耶1922年生于法国布勒斯特,就学于巴黎,是法国“新小说派”代表作家之一。1953年,他发表成名作《橡皮》,1955年因发表《窥视者》获当年法国评论家奖。之后,他在巴黎午夜出版社担任文学顾问,同时从事写作及摄制电影。罗伯-格里耶的独特艺术风格不仅开了新小说的先河,他本人也被后人称为新小说的“加尔文”,成为法国文学史上闪亮的明星。
从1960年代起,格里耶本人也曾创作并导演过数部电影,有《欧洲快车》、《撒谎的人》、《欲念浮动》、《使人疯狂的噪音》等,他于1963年单独摄制的影片《不朽的女人》荣获路易·德吕克电影奖。2006年的《格拉迪瓦找您》(Gradiva)是他生前拍摄的最后一部电影。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