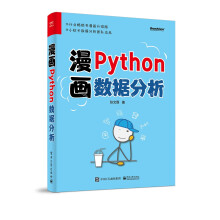郭德纲
郭德纲小评传
郭德纲的半辈子,比一个普通相声艺人的几辈子都要复杂。他这三十几年可用两段话来描述:出身寒微,从小学艺,拜入师门,又被逐出师门,天津卫混不下去了,一咬牙闯荡京城,尝尽人间白眼,苦熬出一个德云社,依靠精湛手艺和青皮气质,打拼出一方天地,开始走上中兴之路。
但造化捧人,它也弄人,郭德纲成了郭员外,就有点势大力沉,顺手给自己圈了个后院,家丁还打了记者。打人不重要,郭德纲把记者当妓女,并大骂BTV,彻底触犯了媒体潜规则,忘恩负义,过河拆桥,这比打人是更深刻的冒犯。所以郭德纲成了三俗,郭德纲下课了,郭德纲关门了,郭德纲下架了,郭德纲道歉了……..虽然现在等来平反,说郭德纲不是真三俗,郭德纲也趁势复出,票房依旧火爆,但经此一役,郭德纲威势大减已是不争的事实。
我说我是看着郭德纲长大的。
这句话不是砸挂,我指的是眼看着他长成大腕。他天津的事我不知道,他跟师傅的恩怨,他是不是犯了经济错误,那是天津人去研究的事。我关注的,是卫嘴子进京之后的奇遇。
郭德纲最美的时光,是在三四年前,他的事业正处于上升期,还是德云社里那个穿着长衫体态微丰的相声艺人。他在台上横扫千军,砸挂一切,什么央视、汪洋、姜昆、春晚,反正他嘴下不死无名之辈。他在台上说得入港,“钢丝”们在台下带着微醺拖出长长的“噫”声。
《论五十年相声之怪现状》、《我这一辈子》、《我要上春晚》,《我要反三俗》《西征梦》,郭德纲所有叫得响的相声段子,都是在那一时期出现的。可别小看这几段,这是新千年里中国相声唯一的收成。
在那个时候,一批青年才俊跟着他走。那个时候的郭,确实有相声大师的雏形,他远离央视,嘲笑歌颂相声,调侃主流意识形态,疾呼让相声回到剧场,很多神圣的虚伪的事物,都在他的讽刺中变得可笑。用王朔的话说,他是站在人民这头的。那时候他正遭到正统相声界的打压,我负责的评论版,曾一年之内发表近二十篇支持郭德纲的评论,一直评到“藏秘排油”为止。
郭德纲越来越火了,天价相声,上电视,当主持,演电影,开铺子,他的名字飞进了千家万户,他成功地摆脱了弱势与贫困。但奇怪的是,在这个星火燎原革命从胜利走向胜利的故事里,不少资深粉丝离去了。
如今,当年跟着他走的意见领袖已绝口不提往事,我猜他们深以为耻,不是因为郭德纲被封了,而是因为郭德纲的“变节”。郭德纲后来在徒弟打人事件中应对失措,举步维艰,跟身边没高人有关系。试想,如果有史航、袁鸿、老六、水晶、陈晓卿等文化达人的指点,那绝对是另一番天地。但他们早就与他分道了,竖子不足与谋。
革命分裂的根本原因,是因为路线有了分歧。很多人期待,郭德纲大师的诞生,能让传统相声的春天到来,能横扫各路伪相声,能战胜某种腐朽的文化。不幸的是,他们很快就发现所托非人,郭德纲自有他的理想,这个人根本不需要革命的浪漫主义。
郭德纲是一个有霸气的人,他彪悍的人生不需要别人解释,他就是要为自己活着。于是,一个成功人士该有的,他都统统超额实现了。他还给自己的别墅圈了座后花园,成了一个员外,还有护院的家丁。一个卫嘴子,终于在京城混出了人样子。
他活出了真我,却也失去了一些东西。他越来越油光满面,一个艺人失去他批判的刀子,太成功了,他都不好意思再批判了。大家开始怀念他从前的相声,这才红了几年呢?
郭德纲骨子里是个老派人,他有深厚的传统艺人的底色。对江湖道义烂熟于心,并且在创业时期将其运用得得心应手。对德云社是这样,对侯耀华是这样,对徐德亮这样,BTV也是这样,他是一个小世界的主宰。但当他遭遇了业主委员会,遭遇了记者采访,遭遇了官家的宣传机器,现代法律和中国政治,这个陌生的世界让他有些发蒙。
于是,何云伟李菁退出了,德云社关门停业了,弟子进去了,书和音像制品都下架了,郭德纲傻了。打了一个记者,骂了句记不如鸡,竟然引发了惊天连锁反应。他在喜马拉雅山下骂了句娘,没想到引起了雪崩。自己怎么就下架了?还有没有天理?政治,尤其中国政治,这回事,他可能理解不了。
BTV一战输得属于完败,和媒体的关系那么脆弱,找不到有关部门灭火,上头连个递话的都没有,在官场两眼一抹黑,郭德纲应该发现了,在京城,一点点虚火根本算不上站稳脚跟。卫嘴子混北京,难呐!
郭德纲一直以来是以相声江湖的规矩行事,如泼皮不要命,仗义出头,有恩报恩,有仇报仇,走的是忠孝信义的路线。但遇到现代法律和政治势力,就两眼摸黑一脸茫然,左支右绌狼狈不堪。他有小聪明而不懂大势,有小勇力而不知进退,还是一传统艺人的底子,所以能纵横于底层而不能游刃于大棋局。
郭德纲的不智在于,他既想在现实世界里成功,又想保持他的狂野的姿态。不跟官家合作,不跟曲协联手,不向BTV低头,要在他的小一统里称王。既不受委屈,又不昧良心,还年年丰收,他太天真了。事实证明,没有哪一块地盘是他自己的。
现在总算复演了,郭德纲接受一轮媒体采访,表达了洗心革面的决心,狠斗私字一闪念,说自己终于长大了。身子放得那个低,尘埃不见郭德纲。总算表态过关了,但德云社没有消停下来。郭德纲开完遵义会议后开始了战略调整,收缩战线,回到剧场,说相声是正事。跟徒弟们也签了长约。他对何云伟李菁仍然很有看法,大弟子出走,毕竟是件闹心的事。郭德纲对此事的反思是,只怪平日太面慈心软,换得别人以怨报德。这个反思相当不靠谱,也许会埋有祸根,但愿别成了“郭德纲掰棒子——红一个扔一个”。
郭德纲有两个诤友,一个是BTV,一个是姜昆。人生得一知己足矣,何况两个。这样郭德纲做事之前,都要先想一想BTV会不会搞自己,这是多好的一位诤友啊。以铜为鉴,可以正衣冠,以姜昆为鉴,可以知兴替,以BTV为鉴,可以知三俗。
天下惟庸人无咎无誉,这些迭荡不平但又不是摧毁性的经历,对一个有天分的艺术家,应该是一份珍贵的财富。当郭德纲真正过完他的一辈子,如果能写一则相声《我这一辈子》,也许才是他最好的作品。而一帮白发老头坐在德云社里面听,那场面应该相当和谐。
2010年9月
海子
一个春暖花开的神话
20年前的3月26日凌晨,一个瘦弱的青年在山海关卧轨自杀,那一天是他的25生日。20年后的今天,他的诗集悄悄地超过舒婷、顾城、汪国真、席慕容,在大小书店里长盛不衰;诗人们聚集在大学校园,对文学青年们讲着关于他的故事,讲他的爱情、西藏、气功;人们说他的死是一个诗歌时代的终结;他的家乡,据说有了海子故居。他本人,长眠在一个什么地方。
一个永远25岁的诗人,已经无可争议地成为一个神话,但对于“被神话”的争议也一直没有停止过。很多人认同“伟大诗人说”,认同“诗歌时代终结”说,也有很多人反对这些,认为任何的神话都是一种异化与歪曲,都会对海子诗歌造成遮蔽,都是对海子的亵渎。我对海子是否应该被神话兴趣不大,我感兴趣的是,海子是如何成为一个神话的?
自杀是诗人的勋章,海子非同寻常的死,最后陪伴着他的《新旧约全书》、《瓦尔登湖》,以及他那伤感的爱情,都是神化一个人的漂亮元素,但是,最核心的推动力,当然是他处的那个时代。
20年前的3月,你可以尽情想象,那是一个怎样的时代,白衣飘飘,以笔为旗,以梦为马,八十年代的狂飙突进与思想狂欢,在那一年里达到沸点。然后一切安静了,九十年代开始了。一个理想主义的年代,就像被谁按下了快门,匆匆闪到了一个世俗的、物欲的年代,中国开始了他远离乡土中国的进程,田园与村庄的衰败正在到来。
海子,这个上天赐给人们的符号,正站在两个世纪的交叉点上。一个神秘的巧合是,他的诗歌永远在歌唱故乡,田野、麦子、天空、村庄成了一个个音符,他诗歌里的神秘与忧伤,与农业社会的气质融为一体。这样一个诗人,在那样一个时代的节骨眼上抛弃生命,于是,他无可避免地成为80年代诗歌热潮与浪漫主义的标志。人们通过怀念海子,通过海子的诗,来表达对一个已逝年代的留恋,以及对一个正在衰亡的农业文明的凭吊。
古往今来的人物,有几人能有这样的机遇?清末的梁巨川、王国维,以死亡完成了对一个文明的送别,他们被写进了思想史。其实,海子和他们的命运是一样的,他们都在历史的路口,亲手给自己埋下了墓碑,他们成了时代的路标。
如此看来,海子的被“过度阐释”,被成为神话,实在是一个自然的过程。同样是死亡,紧随他遽然去世的骆一禾、在小岛上自我毁灭的顾城,都没得到这样的地位,也就很容易理解了。
有些诗人对海子的“面朝大海,春暖花开”成为楼盘广告而愤怒,其实没有必要,成为一个象征,必然要被符号化,被世俗化,被庸俗化。当商人像小摊贩卖格瓦拉一样卖起了“面朝大海”,正意味着海子已正式进入了文化史。
在历史的长河里,又有多少人有机会留下一两个的符号,来供后人解读和解读之解读呢?
2009年3月
浩然
怀念文学史上的“坏作家”
陈冠希经过“艳照门”的疯狂洗礼终于公开道歉,香港“开心果”肥肥经过漫长的挣扎之后挥手告别,法国新小说运动的旗手罗伯—格里耶去世。还有,一个早被人们遗忘的作家悄悄地去了。
“艳照门”堪称娱乐界的奥运会,而肥肥已成为一部死亡真人秀。所以罗伯—格里耶死得有点不是时候,要不是艳照和开心果,这位墙里开花香到中国的法国作家,本可以成为中国文青的一个盛大节日。尽管如此,纪念的阵势依然不小,报纸纷纷辟出大幅版面,携先锋作家、文学壮年以及各路评论家,向这位谁也读不懂的小说家致敬。并津津乐道于他的晚年作品——一部描写变态性爱的小说,还大胆推理出罗伯—格里耶的性缺陷。但是,多少人读过他的书呢?
没读过书没关系,死亡是一场秀,无论你死得牛逼还是庸俗,只要你足够有名,足够有戏,你的死亡都会被塑造成一场狂欢节。
但浩然的死显然没有,他被淡忘了。也有媒体报道,但大多有点漫不经心,只提他写了两部高大全的小说,他曾跟着江青走等等,一副正统当代文学史的调子。谁让他是被批倒的一个人呢。文革结束了吗?所有当年文革的受益者,事后都同样遭受了文革式的待遇。在一些人眼里,浩然这个名字,在现代文学史上已被定了性,是个“坏人”。
我对浩然的去世有些难过,小时候看过他的小说《金光大道》,在大人的旧书堆里翻出来,没觉出好来,可能小孩子理解不了。但我确实吃过浩然的“文学乳汁”,五六年级或者初中时,我们当地的人民广播电台还算红火,还没开始播性病广告,都是“剪裁绣花哪里去,三路到管城”的致富信息。我喜欢听广播剧,完整地听完了一部《田家庄的变迁》(也许不是这个名字,记忆不准了),由浩然的小说《苍生》改编。说的是我熟悉的农村,里面的田保根、田留根很像我的邻居。里面没有政治,有的是一家农村人的个人史,那是我听《白眉大侠》之前最好的收听享受。上世界80年代以后,浩然住在河北三河,办了一本《苍生文学》杂志,开始为业余文学爱好者做义工。帮作者改稿子推荐发表,为71岁的农民出版长篇小说,用十年时间出版《三河泥土文学丛书》。患了半身不遂之后还帮农民作者改稿。不知道别人怎么理解,但这些事情让我很感动。还是我家乡那个人民广播电台,我上初中时,电台还有一个文学节目,主持人是位残疾人,普通话很乡土,每次节目都朗读很多农村文学作者的来稿。他总是把自己感动得热泪盈眶。
在节目里,主持人和那些的农村文学青年总是互相感谢,互相鼓舞,很有理想,也很励志,给我留下了磨不灭的记忆。我对文学还有一些兴趣,应该跟他们的启蒙有关。浩然做的也是这样的事情,他和那位常把自己读哭的主持人,曾给过追逐文学梦的青年农民多少鼓舞,点滴改变过多少苦恼人的人生观甚至人生,我一点也不敢低估。
受过谁的恩,就念谁的好,管他是文学史上的好人还是坏人。我怀念这位被遗弃的作家,而不是罗伯—格里耶。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