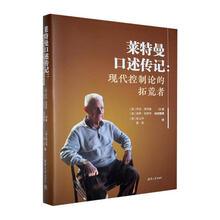“革命者,把我的茶壶也革命了吧?”女子一脸笑意,少年一脸窘样,这才发觉先前读书读得忘情,一激动将茶壶扔了出去。“早该把那帮奴才都扔出去摔得稀烂,亡国奴,亡国奴!”少年依旧激愤不已。女子不知何时,从屋里的柜子里又拾拣出一把茶壶来,壶盖和壶柄处拴着一根细麻绳,她拎起壶盖,往壶口上一盖,来回盖了几次,又转过头冲少年笑笑。少年不解其意,连忙问她,意映,此何意啊? 女子一边拎着茶壶,一边给少年斟上茶。“帽子盖在肚皮上,还能出水;帽子盖在嘴巴上,就出不了水了啊。”女子淡淡的低语,少年却恍然大悟。
“革命要藏在心里,不要挂在嘴上!”少年喃喃自语,若有所思地举起女子递来的茶杯,正待举杯欲饮,恍惚思索间,却杯不对唇,一股脑洒在了手上的那本书上。
少年忙不迭拿衣衫拭去水迹,女子在一旁笑而不语。
红烛初上,夜月当窗。少年悄然睡着了,手里还攥着那本说“革命” 的书,贴伏在自己的胸前。女子轻轻地掰开少年的手,抽出那本书来,因为水浸的原因,有几页上的铅字已渐次模糊不清,趁着烛、月,展开纸、笔,女子仔细地誊抄着那些漶漫的书行——“革命者,天演之公例也。革命者,世界之公理也。革命者,争存争亡过渡时代之要义也。革命者,顺乎天,而应乎人者也。革命者,去腐败而存良善者也。革命者,由野蛮而进文明者也。革命者,除奴隶而为主人者也。”女子轻声念诵,逐字抄录着;少年忽而惊醒过来,痴痴地说,我的《革命军》,我的《革命军》……女子转过身去,用毛笔尖轻蘸了少年的额,笑着说,林少爷,你就是我的革命军……少年与女子笑作一片,楼前清风也跟着呢喃。
他们并不知晓,这一年的4月3日,他们津津乐道的这本《革命军》的作者,已经被官府冠以“乱党”之名杀掉。他们也并不知晓,这一年的8月20日,让官府咬牙切齿的“乱党”们终于有了自己的组织,“乱党”真的要成为一个 “党”了。
而这一刻少年既不是乱党,也不是刁民;既不是什么会的会员,也不是什么敢死队的队员。他只是这个叫“意映”的女子的夫君,他们管这座楼叫“双栖楼”。
1907年春,吉庇路谢家祠内。一大沓《苏报》、《警世钟》、《天讨》等革命进步书刊铺满的圆桌旁,原本簇拥着的一群人,三三两两,摇头叹气地散去了。像一群逐饵的鱼,围拢在水面寻饵时,却嗅到了饵里裹着铁钩的锈味,一溜烟摆头扭尾,自顾自保命去了。桌前立着一名白衫少年,浓眉紧皱,捏拳紧拄在桌板上,一言不发。忽而,一双纤手伸到少年眼前;少年眼光一炯,一把攥住了那只细小的纤手。“意映,你来了。他们走了。”少年颇有些欲言又止的不快。“ 抖飞,瞧我给你带什么来了。”女子从身后飞快地抡出一张报纸来,少年定睛一看,有《中国女报》四个大字。女子又飞快地把报纸藏在身后,急得少年双手来回去夺: “意映,好意映,给我看看罢。”女子轻闪躲,少年几乎一把把她搂在怀里去了。
一瞬,少年意识到是在祠堂里,不好意思地松开了手;女子则握起他的手,说: “走,我们回楼上去读吧。” 他们急急地携手上楼,楼上传来一缕清柔的女声,朗诵着:“本报之设以开通风气,提倡女学,联感情,结团体,并为他日创设中国妇人协会之基础为宗旨。”——少年忽而紧握着女子的手,说:“意映,你一定要加入中国妇人协会。” 女子笑笑说,我在我们抖飞这里课业未勤,学业无成,难当此大任喔。少年拿过报纸,也未接女子的话,接着仔细地读起报来;女子则照例在一旁,间或断章取义地问问,间或轻轻地斟上一杯茶递过去。
这一年春夏之交,少年剪去了发辫,短短的发,精精神神地去了日本;女子与少年时常通信,女子在信笺上落款“双栖楼主”;而信件到日本时,同盟会第14 支部的那个清瘦少年就会匆匆地过来取信,读信,然后回信。奇特的是,这一年夏天,《中国女报》的主编也成了“乱党”,被杀了头。
1911年夏,光禄坊早题巷。署名 “双栖楼主”的女子腆着大肚子,带着一家大小7口人到光禄坊早题巷租了一幢小屋住下。此时,她已有身孕8个月,孩子的父亲就是那个叫“抖飞”的少年。又是一夜夏雨滂沱,滴答滴答的檐头水落在黝黝的青砖上,福州的夏夜,和那个古老帝国的任何一个夏夜一样,漫长而沉郁。
……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