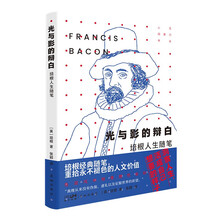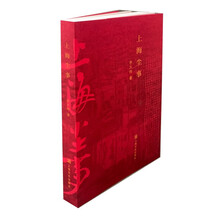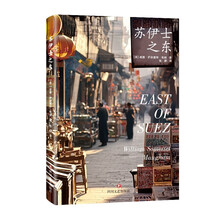张主任还给小王编辑作了交代:“小王,明天把它放在副刊头条发表,再加个编者按:让大家都来关心广大农民工的精神文化生活。”
但我们首先关心的是由此而启动的张得标和小湘的情感生活。 ·
张得标与小湘相对而立,相视而笑。
小湘:“张得标,真想不到你诗写得这样好。”
张得标:“真有那么好吗?”
小湘:“你以后还写诗吗?”
张得标:“不写了,我一辈子就爱你一个人,我一辈子也就写这一首诗。”
棚户区发生的邻里纠纷,往往是因为公共厕所的坑位有限。一早起床,挡在公厕外的大伯大妈脾气再好,内急久了也会发牢骚。
别墅区发生的邻里纷争,则每每是因为公共绿地的面积较大。紧挨绿地的人家难免有“蚕食”的念想,远离绿地的业主常会有“维权”的主张。
棚户区里的纠纷,吵完就完,更不记仇;别墅区里的纷争则往往旷日持久,甚至要走法律程序。
但也有一场别墅区的绿地风波是奇迹般地戛然而止的。
一个高档小区的一幢别墅式住宅前,几位业主围着一位穿着讲究的中年女子争辩着。众邻居反对别墅女主人张女士擅自侵占一块公共绿地,并在上面私建花房。在激烈的争吵中,一位面容娇好的年轻姑娘朝张女士喊了一声:“你对土地如此贪婪,活像个女地主!”张女士听到这声叫骂,犹如五雷轰顶,气得脸色发白,便不依不饶地与这位姑娘纠缠起来:
“什么?!你竞说我是女地主!你可以骂我是暴发户、守财奴,这些我都能忍了,即便你说我是贪污犯,我也不计较,但你千不该万不该说我是女地主,因为你这样严重歪曲了我的阶级出身,侮辱了我的阶级感情。骂一个贫农出身的女人是女地主,是可忍孰不可忍!姑娘,你听着!我祖上三代贫农,那真是‘上无片瓦,下无寸地!’我曾祖父给地主打长工,我祖父是土改积极分子,‘文革’那阵子,我父亲当过县贫下中农协会主席,陈永贵大叔当年与我父亲握过手……”
张女士在“痛说家史”的过程中,泪水一直在眼眶里打转。最后,有点体力透支的她喃喃地说:“我说这些干什么呢?你们不就是要我把绿地腾出来吗?我明天叫工人来把花房拆了就是了,为什么要骂我是女地主呢?”
这一幕也把围着张女士讨说法的业主们惊呆了,他们不知道该说些什么,纷纷走开了。最后离去的,是那位用言语刺激了张女士的姑娘,她甚至想去对张女士说几句宽慰的话,但也找不到恰当的话语,只好作罢。
晚上,张女士把白天发生的事,一五一十说给了丈夫听。丈夫默不作声。
“你怎么不吱声?”妻子问。
“你是急性子,答应明天就拆,现在后悔了吧?”丈夫终于开了口。这回轮到妻子沉默了。
“也只能这样了……”沉默了足足三分钟后,张女士这样说。
在潘家园古玩市场买到一个旧时的漆盒,盒盖上刻着“海日生残夜”五个字。唐代诗人王湾的名句——“海日生残夜,江春入旧年”,状写新春如期而至,旧年却不忍离去的景象。
与此意境相近的,是谢灵运的“池塘生春草,园柳变鸣禽。”春色将尽,夏景已到,树上的鸟已发新声,水边的草却还是“春草”。
两位诗人的可爱,是他们不机械地“弃旧图新”,而是优雅地“喜新念旧”,在喜迎新天地的同时,对行将消逝的时空,也存有些许眷恋,这是能触动古往今来的人心的最柔软处的。难怪宋人吴可要发出“春草池塘一句子,惊天动地至今传”的赞叹。
俄国作家契诃夫写有名剧《樱桃园》(1904),契诃夫夫人在这个戏里演女主角,一连演了四十年。有人问《樱桃园》的主题是什么,满头白发的女演员说:“是人们不想与过去完全告别。”
我见过不少可爱的念旧的人,有的是男的,有的是女的。念旧的人容易体悟“池塘生春草”的诗意。
三个从某省城重点中学毕业的校友,十年后在北京一家茶座相聚。他们中的一个是文学系出身,一个专修哲学,还有一个是学医的。刚一坐定,他们便海阔天空地聊了起来,当然,也聊到了永恒的话题——爱情,而且还从关于爱情的种种定义说起。’
要概括定义,哲学系毕业的自然说得最严谨:“爱情乃是男女在价值观相近基础上的灵与肉的相互吸引。”听到两位老同学的赞许,哲学家苦笑道,这个定义是他从一本教科书上读来的,他也按照这个“定义”恋爱、结婚、生子,结果却并不完满。
文学家听出了哲学家话中的玄机,便用“理论是灰色的,生活才是长青之树”这句名言来转弯子,转到了三人竞讲人世间的爱情故事上。而故事讲得最动人的却是那位医学院的毕业生。其实,他说的是自己行医过程中遇到的一个病例。
有一天,他到一个老年性痴呆病人家去作随访。他问老太太:“老太太,您老伴得病之前有什么征兆?”
“就是记性不好,健忘。”
“您能举个例子吗?”
“例子太多了,举不胜举。”
“那就举个最让您啼笑皆非的好了。”
“我说出来,您不要见笑。”
“不会的”。
老太太便这样讲了起来:
是这样的,约莫是两年前吧,老头儿突然对我说:“我年轻的时候,特别喜欢一个姑娘,她是苏州人,皮肤白极了,眼睛大极了,辫子长极了,身材好极了,名字也好听——叫贝望月。不知道后来她嫁给了什么人了,不知她后来去了什么地方,不知她现在生活得怎么样……”我听了哭笑不得,大声对他说:“老头儿,你怎么忘了,我就叫贝望月,我就是你喜欢的那个苏州姑娘,就是我嫁给了你!”
这个故事先是引出了三个朋友的笑声,但很快他们就沉默了。他们向服务员要了一瓶红酒。三人一边品尝这瓶红酒,一边玩味这个故事。说得最痛快淋漓的是那位文学家:
“不是有恨之人骨一说吗?但也有爱之入骨的呀!”
我有一篇记叙去常熟给母亲扫墓的文章,是这样开头的:“车窗右前方出现一抹青山,便知道我们的汽车快要开进‘十里青山半人城’的常熟。”
“十里青山半人城”,是常熟一个清代名气不大的诗人的诗句,经过同乡名人镝谦益的推介,便成了形容常熟形胜的名句。
我母亲家祖籍在常熟,后来移居到我的故乡杨舍(今张家港市)。我童年时代最深刻的记忆就是对于母亲的记忆。记得我很小的时候,一次半夜醒来,发现妈妈在伏案写字,后来知道她是在写诗,这在我一张白纸似的灵府,刻下了母亲的永恒启示。
母亲常写诗的时候,我还看不懂诗,当我看得懂诗的时候,母亲却不常写诗了。上世纪五十年代末一个中秋节前夕,她倒写了首诗从北京寄给在安徽工作的哥哥和在莫斯科求学的我,其中“一家分三处,两地都思娘”两句,让我感动与感伤了好一阵。
一双热恋中的青年男女牵手而行,沐浴在五月的阳光里。今天是姑娘的生日。小伙子给姑娘送了一个白玉坠,说:“我要让你今天过一个快快乐乐的生日。” 他们决定去听音乐会。他们幻想着,坐在音乐厅里,一定是妙音贯耳,春风荡面。
……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