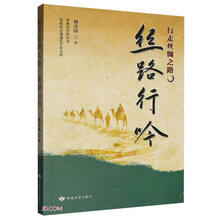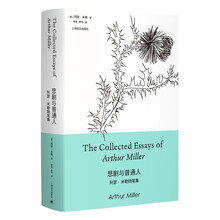我母亲是一个乡下的女人,她一辈子没有进过学堂,所识的几个字,也是我在上小学的时候临时教给她的。她能写的也只有她自己的名字,但她从生活中得来的一些经验性哲理,却让我佩服得五体投地。比方说,她管我的朋友叫草。她所说的草,并不是指我交友的多、滥,而是指我对朋友的态度。在我的一生中,朋友始终是我生命的支点,就像我家院子里的那块小草园,让我倾注了大部分心血。那是我小时候自己开垦出来的,它紧靠在我的窗下。许多时候,我都把路上随意碰到的一两棵草带回家来,种在我的园子,让它春夏秋冬地陪伴着我,成为我生活中的一个景点。
听母亲说,我小的时候,就对草有一种特殊的情感,常常在出去的路上,把一些足以让我痴情的草带回家来种在院子里。几年过去,草竟然也长得郁郁葱葱。起初,母亲以为我少年贪玩,种草玩玩。没想到长大以后,我不但没有改变这种天性,而且还把许多朋友像草一样地带回家来,而且越带越多……从儿时到年长,让这些朋友像园子的草一样,生长在我的生活中,成为我生命的一部分,让周围的许多人,都产生出那种叫羡慕的感情。
我姐姐就曾经几次不平衡地向我请教谜底,我告诉她母亲的话,她很不理解地用眼睛瞪我。我知道,姐姐是不会相信的。她不懂:其实无论种草还是交朋友,遵循的都是同一个道理。你既要给它一个足够的空间,又要给它足够的爱心。不管这种爱心,将来回报你的是什么。比如说我的草吧,我就常常把它局限在我的园子里,保持好它和我之间的距离,让我们彼此有一个相对完整的独立空间。
很多时候,我会花几天时间在园子忙碌,把那些自己长到我园子里的、在我看来是草又不像草的植物,从我园子的草中间清理出去,以便让我的草能有一个更大的空间,更好的发展它们自己。还有的时候,我从早上起来就站在园子,戴上手套和草帽等一些能遮住阳光的东西,像个老农民似的,给我的草松土、浇水、上肥、剪枝。因为我不想让我的草任性地痴长起来,荒芜我的园子,挡住我进出的路。当然,我更不会让它们不小心爬出来,延伸到我来回的小路上……
因为对它们来说,没有足够的力气能托起我的重量,我也没有足够的耐心来顾及它的娇嫩,也许在一次匆忙之间用力地踩下去,让草的绿色受伤,或草因托不起我的分量而发黄枯死。这,都是我无法承受的。因为我觉得,在我的一生中,还没有无能到要草来为我铺路的地步。这样不仅会妨碍我走路的速度,也会让我的心灵受伤。更多的时候,我也许什么都不做,只静静地坐在它们中间,看它们摇摆,听它们拔节,注视着它们在风雨飘摇的日子里,一天天地长大。
这种时候,我就觉得它们其实就是我的朋友。尽管它们都不会说话,但那一片浓浓的绿荫和被风摇曳的姿态,却给我一种清新和温柔的感觉,让我的心在世俗的漂泊之中,慢慢地淡泊了下来,归于宁静。但是,大多数的时间里,我都很匆忙,不是去出差就是忙着赶稿件。有的时候,甚至连园子也顾不上光顾一趟,但那种草的绿色,却常常地萦绕在我的心间,让我没有孤独感。偶尔,我写文章累了,抬起头将身子探出窗外,我园子中的那些草们,就会高兴地摇头向我致意。我要是长时间地不去注意它们,它们也会高昂起头,引来一些鸟或者蜜蜂,发出一点儿响声问候我。如果我所有的事都做完之后,就会沏上一壶新茶,邀朋友一起坐在园子,让草欣赏朋友们的开朗,让朋友欣赏草的沉寂。
因为在我的心中,他们的价值是相等的。虽说他们的外表,长得是如此的不同。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