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见的一点点反而是诗词方面的作品。是50年代初期,看到上海某古旧书店的书目,上面有马先生所著《蠲戏斋诗集》,定价四元,赶紧写信买来。木版六册,是他居四川时,弟子张立民和杨荫林整理编辑的。内容是第一册,《蠲戏斋诗前集》上下二卷,收入川以前弟子抄存的一些诗;第二册,《避寇集》一卷,收由浙江人川时诗,附《芳杜词剩》一卷,收入川之前的词三十多首;第三册至第六册,《蠲戏斋诗编年集》,收辛巳至甲申(194l一1944)共四年的诗。最后编年集是重点,都是60岁前后所作。诗集有自序,是癸未年(1943)年底所作,刻在第四册之前,说明自己作诗的主张是行古之诗教而惩汉魏以后之失,就是说,不是吟风弄月,而是有益政教。并解释老年多作的原因是:“余弱岁治经,获少窥六义之指,壮更世变,颇涉玄言,其于篇什,未数数然也。老而播越,亲见乱离,无遗身之智,有同民之患。于是触缘遇境,稍稍有作,哀民之困,以写我忧。”可见内容是走杜工部和白香山一条路。
我大致读了一遍,印象相当深,可以分作几项说。其一,突出的印象是诗才高。这可以举两事为证一是笔下神速。以癸未下半年为例,中国页49页,一页收诗以七八首计,总数近四百首,一天平均两首半,其中有些古体篇幅相当长,这速度在古人也是少见的。二是语句精炼。比如五律,首联可对偶而通常是不对偶,马先生不然,而是经常对偶,并且对得工整而自然。其二,是学富,诸子百家,三教九流,信笔入诗,所以显得辞雅而意深厚。其三,确是言行一致,很少写个人的哀愁,而是多少有关政教。总的印象是,与同行辈也写旧诗的人,如沈尹默、陈寅恪、林宰平诸位相比,马先生像是更当行,更近于古人,这在梁任公“新民丛报体”已经流行之后是不容易的。勉强吹毛求小疵,是纳兰成德在《渌水亭杂识》中评论苏东坡的话:“诗伤学,词伤才。”马先生正是“学”过多,因而气味像是板着面孔说理,而不是含着眼泪言情,换句话说,是缺少《古诗十九首》那样的朴味和痴味。
展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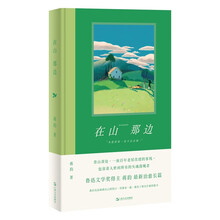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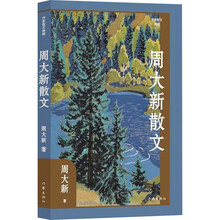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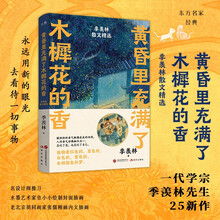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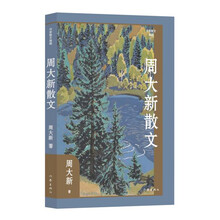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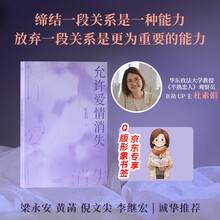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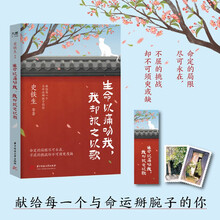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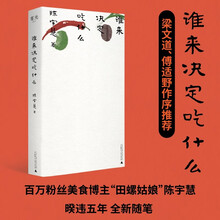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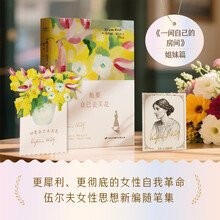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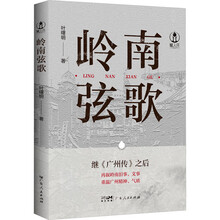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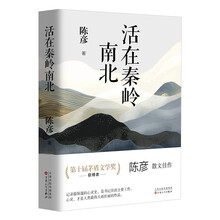
——季羡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