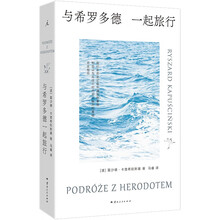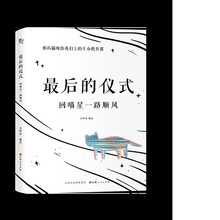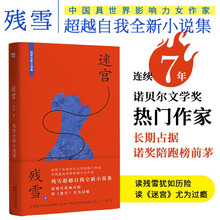我现在已经有妻了,但我在八九年前,或者说不定是十年前的时候——虽然到现在还痛苦地静默——却曾恋过别一个女人的。
虽然这事使我对于现在的妻感到做了什么很大的恶事似的隐痛,但一面却又常常想着伊;从自己的心的深处,浮现着伊那可爱的风姿的时候,,也是常常有的。
这事对妻固然应该抱歉——其实也只因为在我的性生活中,伊已做了先驱者,留下了深的印象了的缘故。但是为了这事,岂仅使我对于现在的妻有着欺负之罪么?我们两人的牵连的生活,也就因此有着永久补缀不好的伤痕了!
伊是东京神田的一个叫做“朝日”的下宿的主人的女儿,那时是十九岁,因为长得高大,而且有了女人的情态,看去已像二十多岁的人了。伊的父母都唤伊作桃娘,所以住在下宿里的旅客也都模仿着唤伊为桃娘了。我是在下宿里住过一年以上的老顾客,又且常常和伊说笑的,所以曾经给伊定下一个特别的称号,叫做“Knife”。这在当初,原只有我和伊两人间私下运用的,后来伊的母亲也盲从地仿用起来,最后连伊的父亲也仿用了。但是我们在春季里,因为剥削桃皮时候,发见桃子与knife的关系而命名的趣事,同居的旅客不必说,便是知道使用这称谓的伊那父母俩,也还是莫名其妙的。
我在东京,第一次跑进我眼孔里来的女子,固然并不是伊,但在我的眼中,乃至心中,留下温美的印象,而又受过爱的光辉的照耀的,伊却是第一人了。
记得是一个秋天的傍晚,太阳的稀淡的光芒,雾一般的落在凌乱的屋顶和街上,我从、一家杂货铺的拐角上弯入小巷里,立住在写着暗淡的“朝日”两字的下宿门口,漫然的问道:“这里可有空着的房间么?”
“有的。”从右边的房里发出这样的细轻的声音来;接着便现出反问着“几席的呵?”的一个说中国话的日本女子。我对于伊的说中国话,初颇有点生气,以为在蔑视我。后来知道这家是专收中国学生和朝鲜学生的下宿;而且在伊的温美的态度中,体察到伊那对于初来的不谙日语时中国学生的厚意,这才反恶为好地意识到伊的可爱了。这瞬间的可爱的印象,不仅当时深深的打动了我的灵魂的全部,便是现在一翻一翻,常常从回忆中浮出伊的影子,也很与这第一印象有着难分的关系。
从种种举动上看来,伊原是一个轻浮的女子,据说从伊祖父起就在这都市的东京生活的。但是因为有着极度的聪明,伊那轻浮的弱点就在我的观察中整个地消去了,宛如对着残废的亲友,因为有了人情的融和,而忘却他形体的残废一样。我在下宿中住了一年,原很受着主人和同居的旅客的尊敬的,即使说笑,也只说些普通人所能听而惯听的说话,女人的身上是从来不敢惹上去的。但是我这卷藏在自己心窟中的对伊的一丝柔情,却不知从什么时候或什么地方,已经被伊侦知了。伊有时也玩笑似地对我说些挑拨话,例如晚上叠被的时候问一声“寂寞么?”之类。但我被处于这样的情景中,总以宽宏亲和的态度,自己守着沉默,或消极的说一声“并不”;至于以为这是伊的劣点,可以去呵责或利用的心思,更是没有了。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