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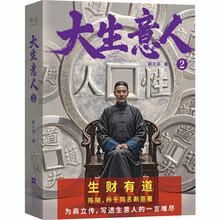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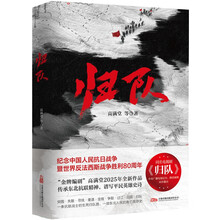


佛陀问阿难,你有多喜欢她。
阿难回答:我愿化身石桥,受五百年风吹,五百年日晒,五百年雨淋,但求伊从桥上走过。
我,白素贞,倾心一人之姿,几近阿难佛心。念于此,怎能不住狂笑。
可我还是妖。人妖殊途,我并不糊涂。
一位我的前辈,取道西域,在求真经的路上,曾对他的四位摸样古怪的徒弟说过这么些个颇有哲理的话,"人和妖都是妈生的,不同的是,人是人他妈的生的,妖是妖他妈生的……做妖就象做人一样,要有仁慈的心,有了仁慈的心,就不再是妖,是人妖。"
啃烤白薯,仰望星空。
对。一袭袈裟,一串念珠,一双艺鞋,一只盂鉢,一身坚骨,一杯愁绪。
当年的我,也是个不折不扣的文艺青年,治愈系和尚。
天空长着好多痣,一闪一闪亮晶晶。
放下远目,转看能忍,他熟睡的摸样似幼兽,蜷曲身形,将己紧抱。
那姿势呵,像在抵御人世的虚妄。
不自觉唇角微扬。
水花四溅,把情漾开。
蛇舌,深含细吐,苒苒菲菲荡荡,以吻封缄。
他竟睁开眼,看我,那眼神,那眼神啊,熟悉已极。是了,因他的眼里有我。以真气喂食于他:官人,日后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切莫忘怀。
这是我的心语,他自然听不见。
听不见也好。
听见了麻烦也有。
是哪个僧道曾说:
压根儿没见最好,省得情思萦绕。原来不熟也好,就不会这般颠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