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开始他确也想过求助这城市的某些救助系统。他拨了一一九。与那些戴着荧光夜壶帽、穿着熊皮般防火风衣的魁梧大汉印象不同,是个甜美的女孩嗓音。他告诉那女孩,现在他这里有一具刚断气的尸体,他想要捐出死者的眼角膜和肾脏。(或者还有其他可捐的器官?)
女孩耐性地向他解释,尸体的运送(或遗体捐赠)好像不属于一一九灾难救助的范围,似乎应该直接找遗体所捐赠之医院请派救护车。
噢,好,那我知道了。谢谢。他说。
女孩说您打算捐给那间医院,也许我们可以帮你联络……
不,不用了,这样我知道该怎么做了。谢谢你哟。他讷讷地挂了电话。
他将他母亲抱上轮椅。那具身体出乎想像的小且轻。他母亲像
临终前整个放弃生存意志的那一段时光,安静而听话地任他摆弄。
真是没有一个,生与死之间的清楚界线哪。他寂寞地想着。
他替尸体戴上毛线帽,围上围巾,并且套上她那件鼠灰色的开襟毛衣。
他记得最后一次,他推着他母亲从医院坐捷运回家。他母亲从合上的电动车门的玻璃窗上看见了自己的身影,似乎大受刺激:
“怎么我变得那么瘦?”
反复喃喃自语。简直像骷髅一样。
现在他推着他母亲的尸体出门。他母亲如同生前一般瞪着灰色的眼睛,像受了什么惊吓。
他后来回忆:那恰好是那个晚上最后一班捷运了。他推着他母亲走进冷清、空旷,因为插票入口大厅几乎空无一人而显得四周金属墙有一种科幻电影的感伤氛围的捷运站。
那晚的温度,恰好是你坐在捷运车厢内对着窗玻璃哈气,会有一阵白雾将你自己的影像盖去的冷天。他总是不可避免地想着尸体融化发臭流出血水这类事情——虽然他推的并不是一块化冰中的冷冻猪肉。他并没有循正常电扶梯下降到站台。他是搭一种专供乘坐轮椅行动不便者搭乘的电梯。他母亲被推进电梯时突然把嘴张开——他还真被吓了一跳——也许是轮椅过电梯门的凹框时颠震所致。他想她待会儿不会在车厢里用一条毛巾(原先放在轮椅背后的折袋)盖住他母亲上仰而口微张的脸。
电梯门打开时他听到一阵尖锐响亮的哨子声,那是捷运车要关上门开走啰的最后警告。他发狂地推着轮椅冲进那下一瞬即合上的电动车门。他看到他母亲盖着毛巾的头颅前后摇晃了一下,然后列车开动。
他这才想起这是最后一班车了哩。
好在有赶上。他有点孤寂地意识到,虽然是他和他母亲一块完成从电梯口穿过站台冲上像从来没停止只是在一种移动瞬间穿越一跃而上的捷运车厢,此刻喘着气(带着轻微的侥幸和安心)的只有他一个人。
如果没赶上这班车呢?
那大不了就是不捐了吧。眼下这具身体上可堪摘下剪下再利用的眼角膜或肾脏或其他什么的,就像那些放过了赏味期限的保鲜膜包的切块水果,摸摸鼻子便丢进垃圾桶了。他就得再推着他母亲的尸体,走出那个捷运站,回到他母亲的公寓里。
如果是那样的话,他可要好好地补睡一个长觉(他多久没合眼了)。先把尸体这一类事情搁在一边,好好睡一觉再说。
不过现在他总算是赶上了这最后一班车。
车体摇晃着,他觉得这摇晃仿佛将车厢上单调冷寂的日光灯光照,像筛篓子摇晃谷穗乱洒。像他在第四台看过的那些好莱坞影片,潜行在阴暗下水道的男主角们和在上方搜捕他们的特种部队对峙着。一边在光的世界,一边在依稀只见管线轮廓、胶靴踩踏积水,还有老鼠沿耳际窜爬过的阴暗世界。双方僵持猜测,最后忍不住开火。那种停火后光柱从冲锋枪上下交驳乱扫的砖墙间的弹孔中筛漏而下。
又或者像所有的那些恐怖分子在人口密集的某处(芝加哥市市中心;一架七四七的客机;美国海军的深海核子动力潜艇;纽约联合国总部大楼……),装设了一颗毁灭性的定时炸弹(从俄罗斯乌克兰边境劫走的核弹头、国防部秘密研发的违反国际化武限制条例的超级神经性毒气,或是扩散出去的伊波拉病毒……)。这些烂情节永远只让他铭刻难忘着某种自然视觉下无法看见的光的造型:即透过男主角的分光镜,可以无比华丽又恐怖地看见,环绕在那颗静蛰于黑暗中待拆除的炸弹四周,是像蛛网环织的红外线触动引爆光束……
他觉得他和他母亲,还有这车上这些无明陌生且一脸冷漠的末班乘客,仿佛就被那种摇晃中散落下来的紊乱光束给裹覆在一块。
——没有人知道我们这之中已经有一人停了鼻息了吧。
他这样敌意地瞪视着一些摊着愚蠢惫懒面容的家伙,没有发现空空落落的车厢上,只有他一人站着。
(他母亲在那条毛巾下张大了嘴)
突然之间,他在那些家伙中,发现了一张脸。像显微镜的调焦,由朦胧、重叠、双影,最后无比清晰。
是傅达仁。
“咦?是傅达仁吔。”他几乎要轻呼出声,原来傅达仁也会跑来坐捷运。他发现他竟下意识推了他母亲的肩头两下。“妈,醒醒,你看,傅达仁跟我们坐同一班车吔。”像是她真的会一脸困惑睁开眼为了贪看热闹。像他小时候,她带他坐公交车,会大惊小怪地将他摇醒,“你看窗外,那里有车撞死人了。”
那个傅达仁穿着一件白色西装裤和白色休闲鞋,拿着一支拐杖拄在两腿间。眯着眼笑着。仿佛蜡像馆里的陈列,知道自己命定会受人侧目。其实他坐在这样光照的人群中,活脱是个老人了。
一脸的老人斑。
灵光一闪地,脑海里突然浮出一个画面:那是在极黑暗无光的深海底下,一个庞然巨物艰难沉重在转身的画面。因为近乎无光照情形下的摄影,且水作为充满空间的介质,使得那个庞大物事翻身以臀部背对镜头时,有一种天摇地动巨大压力造成的耳鸣印象。
怎么回事?是一只鲸吗?
他突然想起来:那是印象中他母亲最后一次神智清明地坐在电视前。他记得他母亲拿着一条脏手帕在擦眼泪。他想起来了:那时电视画面播放的是一艘潜水艇。
无垠深海中一艘孤零零的核子潜艇。
在那一瞬间,许多疑问同时浮起:那些他不在身边的时光,他母亲都在看什么样的节目哟?他母亲是为了什么在哭?还有,那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节目?为什么播放着深海底下的一艘巨大的潜艇?(是 Discovery?还是那些潜艇喋血类型的好莱坞烂片?)
他难过地想:他母亲这一生,可以说是全白费了。
他记得他母亲告诉过他:她小学毕业那年,曾因为获得全校第一名,而和全台北市所有小学第一名的小朋友,被市长招待搭飞机绕行台北上空一圈。
他实在无法想像那样的画面:他无法想像他母亲这样一个邋遢肮脏的老太太竟曾经是个第一名毕业的小学女生?那是什么样的一个年代?为什么区区几个第一名毕业的小孩,便可以蒙市长陪伴一道搭机升空?而且是这样奇怪的飞行方式,并非拿到“台北—泰国”来回机票或“台北—澎湖”至少“台北—高雄”等等三日游或怎样配套方案的招待,而是由台北松山机场起飞,飞机在台北盆地的上空滑翔一圈(飞机上所有的第一名小朋友都像土包子那样鼓掌欢呼,对着下面变得小小的淡水河或台北桥或观音山指认着),最后仍是在台北松山机场降落。
似乎那样大费周章升空的目的,就是单纯为了“坐飞机”?
也许他确曾看过一张照片:他的母亲穿着土黄卡其制服,颈上系着一条草绿色童军领巾,留着西瓜皮短发,和另外二十个一式穿着的小学生一起蹲在一架美军老母机的机舱门前,一旁还有一个穿西装戴黑框眼镜的中年人(那是当时的市长吗?),还有一个戴防风眼镜飞行帽穿皮夹克的年轻飞行员。所有的小朋友都咧开黑的牙齿冲着镜头笑着,只有他母亲像一只瘦弱的小鸡,惊恐地睁大了眼……
当然他母亲并没有这样一张照片。
那些闭目养神散坐在车厢两侧急速冷却树脂座椅的陌生人(那个傅达仁不知在哪一站悄悄地下车了),在这样梦幻般的摇晃与窗外鬼哭神号般的裂风尖啸声里,突然一个个变成像那些庙宇两侧,陪祀陈列底座注记了捐赠人姓名的泥塑罗汉力士。窗外无比的黑暗。这些不知情的送行人在这封闭如腔肠的车厢内,在交错反差的晦黯光照下,脸上像敷了金箔,闭目的神情像那些烈焰焚烧的经卷绘画上的菩萨的脸,那是一瞬间悲悯,一瞬间淫欲贪欢,一瞬间嗔怒可怖,下一瞬又平和枯寂……
但是他母亲却不成材地在那轮椅和旧毛毯间萎顿塌缩。他甚至觉得她正在融化中。简直像是千里迢迢送一块冰块而不是一具遗体。他简直不敢想像待会到了医院,一揭开那毛毯,她母亲的身体还会完好无缺地在那吗?
医师,这是我妈的尸体,她吩嘱我要把它捐出来。
好,把那毯子掀开来吧。
是。
啊,怎么是一副化冰的猪下水嘛(剩下肝和一团白肠子)。
其他的呢?
来不及都化掉了。
……
展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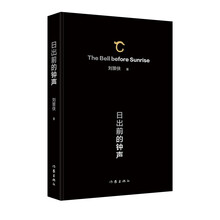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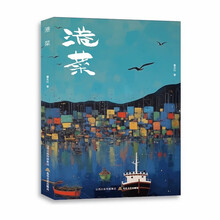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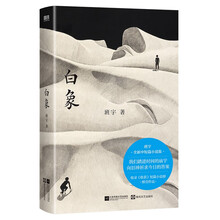
——《深圳晚报》
《遣悲怀》是我心目中新世纪台湾小说第一部佳构。
——王德威
骆以军的眼睛就像核爆,所有东西被他目光一扫就全部变成废墟。
——朱天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