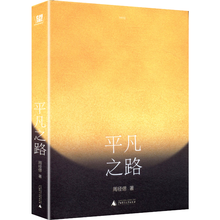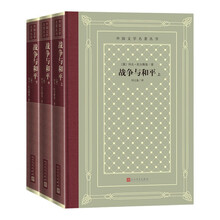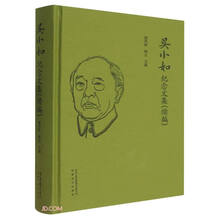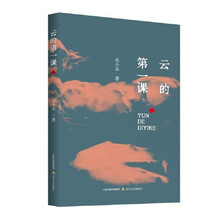从上海的老北站上火车,火车上充满了汗味、尿臭和脏物,行李架上塞满了摇摇欲坠的包裹。两天两夜,不能躺下甚至连一口热水也没有。天地交接处在车窗外缓慢地旋转,过河,宽的窄的;看见山了,石山土山秃山绒山;又是平野,牛羊和包着头巾的女人。如此循环往复以至无穷。
哈尔滨,下了火车,再上火车。小兴安岭绵延起伏的山峦,黑色的和白色的森林,河流峭壁苍鹰蓝天,如诗如画。浓黑的夜里,,车窗外黑影幢幢。也许是第二天的清晨,也许是傍晚。火车停在了这条线路的终点上,一个地图上标着乌依岭的小镇。
只有坐汽车了,敞篷的解放牌。五六个小时在崎岖的山路上颠簸,黄尘盖头,如蒙难的囚犯。土路也到了尽头,一行人打闹着呼啸着走进无边的荒原。月光下,身边的矮树丛里幽光点点,那是随行的孤狼。喧嚣沉寂了,疲惫的脚如两条木棍机械地一前一后摆动,时而,一声惊恐绝望的尖叫,夜便如地狱一般阴沉可怖。
远处,隐隐约约几星灯光,黑暗中渐渐地放大。我们知道,到了,那个我们千里迢迢离乡背井前来落户的村庄。
在这个地方,我们生活了五年或者十年,或者一生。
许多年后,我一直在想,是什么驱使我们心甘情愿走向这个小山村的。从父母拘谨的工资收入中挤出钱来,每年或两年一次往返于东北和上海的千里铁道线上。信仰服从,户籍制度,还是社会力量的惯性作用?
这些年来,我和我的那些插兄一直在说要再去那个地方看看,这已经成为了我们的一个经常性的话题,一块心病,一个人生的憧憬。我们有了一些钱,足够到那个地方去十次二十次,时间也会有的,挤出一年中的公休假就可以了,可是我们没有成行,至少至今还没有成行。行期遥遥,也许永远也只能是一个话题一块心病一个憧憬。
为什么?说不清楚,无法说清楚了。
我感觉我们老了。衰老的明显的标志之一就是沉湎于往事的回忆。那时候的风、雨、雪,茅屋和石上的青苔,太阳照在麦苗上的气息,夜间发红的月亮和黑洞洞的山冈,还有人物的一笑一颦,小小的玩笑,过错,令人羞愧的话语……纤毫毕显,丝缕可析。
我们像孩子似的问年轻的一代:你们有吗?你们知道黑夜的森林的样子吗?
回忆成了我们对抗当今这个物欲横流的世界的武器,我们知道,光荣不再属于我们,世界不再属于我们,属于我们的只有往昔的回忆,对苦难和幼稚的酸涩的回忆。任何别人所没有的东西都可以成为向世人炫耀的资本。
这或许是雨离我而去的原因之一吧。雨无法面对我的衰老,她还年轻,她不需要回忆。所以她走了。在一个阳光明媚的早上,我还在床上沉睡的时候,她为我准备了面包和果酱,在一杯牛奶下压了一张纸条,上面写着四个歪歪扭扭的汉字:
我要离婚。
雨是我的第二任妻子,小我十三岁。这是一个比较尴尬的年龄差距。按照常规,应该是我给予她更多一点,然而恰恰相反,结婚以后我的生活几乎全由她来支配了,从日常食谱、起居时间、衣着打扮到待人接物、娱乐活动,她都一一对我进行调教,力求达到标准,她要把我拉到她的那个年龄层次,从而进入和适应她的生活圈子。就连夫妻生活,雨也有她的一套。时间、地点、氛围,准备阶段,适度的外在刺激,每每都经过周密的计划。还有那些花样翻新的体位,往往能造成意想不到的效果。
真是太好了。雨长长地叹息一声,心满意足地睡去。
计划的某个环节出了偏差,她也是长长的一声叹息,真没劲。
不管是满意还是没劲,我总有一种不到位的感觉,好像一个小徒弟老是在师傅的阴影下提心吊胆。这种时候,我会不由自主地想到杉。想到我和杉那段漫长的恋爱和极为短暂的婚姻。对一个男人来说,这样比较有助于加深对女人的认识,从而认清自己的处境。
可是,一切的一切都无济于事,雨还是走了,无可挽回地离我而去了。和大多数这个年纪的女孩一样,雨有自己的价值观和婚姻观,在她认为应该放弃的时候,她会毫不犹豫地做出果断的决策,就像社会上每天每时都有人跳槽一样,她像鸟儿一样飞向她向往中的大树。这就是她们这代人和我们的不同之处,这是无法抗拒的规律,我们只能听从于命运。
独自一人的我,从此开始夜夜与梦境作伴。
有时候,我居然分不清梦与现实,孰真孰假。梦境是真实的世界呢,还是现实只是一场梦?其实分清两者的界线并无多大的意义,因为,做梦的时候,我们同样存在,它占据了我们半个人生。梦与现实就像白天和黑夜一样,相互交替缺一不可。
然而,令我感到惊奇的是,绝大多数的梦境都与我三十岁以前的那段时间有关,仿佛时光倒流,人生重复。
空罐头做成的柴油灯,火苗摇晃,人的影子在墙上跳舞。黑烟从灯上升起,在纸糊的天棚下回旋,气味刺鼻辣眼。一个奇怪的冬夜,雪原上传来冰凌折裂的悠远悦耳的声响,马爬犁在雪上轻盈地滑过。
我箕坐炕上,占据炕桌的一角。炕面热透,隔着焦黄残破的炕席,屁股焦灼不安地挪动。对面,荃的脸清瘦苍白,缀有淡淡的雀斑,尖下巴,细颈。他盘着腿,双手垫在臀下,一如往日的拘谨。我嗅到了何身上汗馊和黄烟的气味,热烘烘中夹点酸甜。何的头发剪成参差不齐的一圈马桶盖,一张娃娃脸,胖圆红润。
我看不清自己的模样,弄不明白为何如此清晰地关注何和荃的面容,更诧异夜的黑暗沉寂。
杉在外间灶上熬汤。腌肉的香味已绕过门框登堂入室了。我看见杉半蹲着,侧转脸查看灶火。灶台上的油灯照亮了她的脸面,滑润光泽,五官生动表情达意。她的下部被棉裤紧裹,在火红的灶火勾勒下,硕圆醒目惊心动魄。灶火不时溅出几点火星,洒在她的脚边。
……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