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想到这次旅途会是一趟死亡之旅。
最近常有一种家毁人亡的感受,不但父亲躺在死亡病房,母亲重病,我和丈夫也愈行愈远了。不知道到底为什么?在我写的故事里,米诺斯(Minos)曾激怒海神波赛冬,而我什么都没做。我做了什么?
父亲的悲剧与家产有关。他出身中国北方地主家庭,因最得祖父疼爱,在祖父过世前得到口谕,分得最多财产,他的兄嫂不服,打算加害他,在祖母的指令下,先躲到台湾。又其实,这段故事是他自己的说法,我母亲则说,真正的原因是因为一个女人。总之,他来了台湾,改名换姓,娶妻生子,但生性风流的他,在我儿时不常回家,与母亲终生吵闹分合,后来他索性搬回大陆老家,但悲剧再度重演,他仍然和大陆家人因分财产而闹得很不愉快,他认为亲妹妹骗去他的积蓄。他因而气病了。一个人返回台湾,去医院做检查,才得知已是肺癌末期。
他不相信自己得癌,或者,他不想相信。每天照常爬山,而且还找到属意的情人。今年起,癌细胞转移了,他无法自理生活,情人避不见面,母亲也病了,两人皆无人照顾,姐姐只好接他到香港住。
这就是我来香港的原因。
有家归不得。偶而喃喃自语时,这几个字便从父亲口中跑了出来。有家归不得,那是何感受?而他的家在哪里?我的家又在哪里?我总觉得家这个字如此像旅行社的旅游景点介绍,充满动人的想象和憧憬,但不能完全当真。
很多人都说,“家”或“成家”很重要。但家是什么?日文的家族“□□□”,谐音像“枷索箍”,听起来像是家人必须绑在一起?中文呢?曾经有一个人告诉我,家是什么?家是宝盖头,下面养了一只猪。我当时笑了很久,现在也笑,但仍然不甚了了,宝盖头下面养了一只猪?
最后一次看到父亲是什么时候?说了什么?是几天前,但他已无法说话了。之前的最近,我和他还有过短暂对话。
前一阵子你好像出版了一本新书?又是什么书?
又是什么书?这“又”字听起来像谴责,父亲的确这么说过。
又是什么书?仿佛我像个变把戏的人,又变了什么把戏?我那时只回答他:就是一本书啊,没什么。我不想多作解释,他从来没读过我任何一本书,我猜。我也没问。我们从来没聊过天。
唯一的例外是婚后,父亲与母亲到德国拜访我,那一次,我破天荒和他朝夕相处十来天,和他说了一些话,因而陷入情绪低潮,有一天竞责问起他,童年为何处罚我?他完全不记得了。在我的丈夫Q面前,他向我解释,但我又不想听。他难为情地走开,后来在我们家附近的森林走失了。
那时我便对Q说过,我的父亲不是父亲,他不知道怎么做一个父亲。
但我也不知道怎么做一个女儿。我多么希望能和他谈心,多么希望。希望已不足形容,应该说,多么渴望他能拍拍我的肩安慰我,或在人生道路的转折点上鼓励我。
我渴望这些,真的渴望。
其实父亲不知道,我常常书写我和他之间的关系。也曾像卡夫卡一样有过质疑:还要再一次书写父亲吗?多少次了?父亲大人,我在回忆里写他,我在梦中遇见他。我是不是终生在追寻一位像父亲一样的男人——像父亲那样爱我或不爱我的男人?
十天前,我坐在他身边的小躺椅上,父亲突然以悲伤的眼神看着我,我因从来没看过这神情而震惊不已。难道他知道自己的生命走到尽头了吗?
父亲那时认真地表示,自己的后事想以风葬,就把他的骨灰撒在台湾海峡上吧。不但别人,他也觉得,自己什么都不是,既不属于这边,也不属于那边。
还有,他说,希望骨灰不要置入骨灰坛内,他不喜欢坛瓮。那木盒可以吗?我那时突然无厘头地问起,还有,譬如椰子壳呢?可以,他点点头,但立刻阻止我再说下去。他不喜欢这些奇怪的细节?
他似乎也不习惯谈自己的后事。
你就常来看他吧,这次是真的没多久可活了,姐姐说。
那么多年以来,我一直在心理分析医师那里抱怨,儿时父母如何没爱过我,他们忙着生计和外遇,从来没有时间照顾孩子,转眼之间,已到了我必须照顾他们的时刻?
三年前,姐姐第一次打电话来,那一天,我刚好在湖边慢跑。她说,爸不行了,癌症末期,只有三个月可活。我如遭晴天霹雳,呆站在湖边的小径上,望向火红的夕阳,湖边的群鸭扑扑地飞去,我一边跑,一边哭了出来。
那时心想,从小没有家,现在连父亲也没有了。
在湖边哭完后,我便没什么感觉,仿佛变成一个没心肝的人了。
两年前,有一天去做超音波检查时,权威医学专家断定我得了癌症末期,立刻当场联系医院准备开刀,我打电话给Q,他没接电话,我写了短讯给他,一个字:坏。我回家等待入院。那几天,我以为自己行将就木,写下了遗书,内容很简单,把身外之物全留给父母。但人院后,医生却说,不必开刀,不是癌症。根本不是。
曾经死过十天,又活了过来。那些天,我都在读佛经。我猜很多被宣布得癌症的人都会读佛经或《圣经》。我猜,死讯极难接受,但总有一天还是得接受。我想象父亲如何接受自己的死讯。
即将失去父亲的我想起那年的Q,他的惊慌失措,有一整年吧,他的父亲还未死,他已经如丧考妣,常常发呆、叹气。他父亲死时,他一个人坐在教堂哭了好久,我在他身边却未安慰他。现在才能体会一点点他那时的心境。
刚来港去探视父亲时,他才做完十二次化疗,戴顶帽子,看起来仍然像一个英俊的蒙古战士,他有一张男性的倔强的脸,那张脸害死了多少女人。我母亲,以及无数的外遇。他一生只对女人感兴趣,各种女人,奇怪的、矮小的、精悍的,环肥燕瘦,无一不可,而母亲是那个受苦的人,她一辈子受这种苦,但仍旧不死心。她永远不死心。
……
展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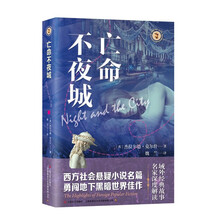
——陈冠中
这是一个超速旋转的残酷星球,一个暴力失衡的恐怖都市,恶魔逼至眼前,如影随形——我并不知道,恶魔即我。
——虹影
为何写作?为谁写作?写作什么?这全是每一个作者都要坦诚面对的根本问题。陈玉慧回答这些大哉问的办法就是为自己设定了一个埋身割喉的极近距离,毫不懈怠,步步进逼,直到生死关头,这才爆发出了如此精彩而又如此深入骨髓的写作沉思。
——梁文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