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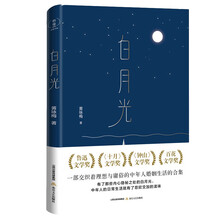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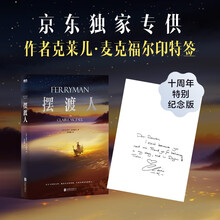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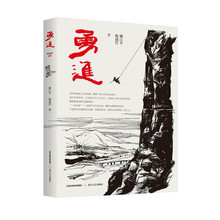




石坂屋
边风飘飘那可度,绝域苍茫更何有。
——唐·高适《燕歌行》
一
我到凉西戽庄子不到半月,就碰上生产队组织施工队的事。
施工地点很远,差不多有1300百多里路,在天山东段博格达山的余脉与东疆戈壁交接的地方。那儿有一座新开的矿,叫卡卡斯雅矿。卡卡斯雅的维语意思是“荒凉的地方”,这意思只有庄子上的几户维吾尔族社员懂得。其他人都把它叫成了卡卡子。卡卡子,当地汉人和回回的土话,就是近乎角落、旮旯或夹缝的意思。
凉西戽庄子地处天山北麓,快接近古尔班通古特沙漠边沿地带了。庄子里的人见过些世面的寥寥可数,孤陋寡闻得很。能把手伸到1000多里地外去,全仰仗了一位姓范的河南大工。这人,除了生产队副队长谷发以外,谁也没见过他。4天前谷发跑了趟县城,想揽点副业活儿。转悠了两天,一无所获,夜里宿在县上的车马店,碰上草湖庄子施工队的车户耿昌,便打听哪儿还能找上施工活儿。旁边一个人过来搭讪,自我介绍说他是大工,能联系上活儿。就是施工地点远了点儿,远虽远些,但油水很大。今年先盖四栋平房,明年还有十几栋房的任务,往后还要盖楼房、俱乐部、水塔,是个长活儿。他问谷发愿不愿去,愿去,只要拉上一支30人的队伍就行。谷发自然愿意,两人便到车马店旁边的小饭馆细谈,那老范扔了l。元钱给开票的,要了几盘肉菜,又买了一斤地瓜白烧,两人边喝边谈。谷发心里不甚踏实,杯间想套套他的底细,那老范把脸一沉说,“信得过俺,就干,信不过,拉球倒!俺不稀罕你们,少他奶奶的问东问西!”说完生气要走,谷发忙扯住赔不是,于是两人便约定,一个星期以后,也就是第7天的早晨,谷发带了人马到乌鲁木齐火车南站跟他汇合,然后立即上火车。他只在车站等两个小时,过时不候。
为了凑够一支30人的远征队伍,生产队在马号院子里开了个动员大会。我原以为这样的会一定庄严肃穆得很,到会场一看。简直一盘散沙。主持会的是支部书记老福禄,讲话蹲着讲,好像边拉屎边跟人聊天似的。下面没有人听他讲,东一堆、西一堆,嬉笑打闹,乱作一团。
他动员完毕,谷发就让大伙儿报名,喊了几声,没人响应,便笑骂起来,“嗓门眼都让×毛塞住了么?昨都不言声呢?还要我一个一个地点么?”
他骂完,大约过了一两分钟,人堆堆里洋洋干干站起一个人来。这人,庄子上的人都叫他花儿铁,他的相貌十分奇特,下巴颏尖锐地前伸,侧面看,超过鼻子许多,眼睛老是眯缝着,明明没有笑,也觉得他好像在笑,他的一条腿有些瘸,站起来后身子歪斜着,吊儿郎当地说,“寿娃子,把你铁爷的名字写上吧!”说着,弯下腰跟旁边一个婆姨嬉笑几句,忽然又挥起手喊一声,“还有,石牡丹,她也要跟我去哩!”
他这一喊,满院子哈哈大笑,连老福禄也仰起花白山羊胡子,跟着笑。石牡丹是个寡妇,丈夫刘魁两年前得急病死了。因为我们和她在一个作业组,知道一点她的情况。花儿铁喊完,她的脸绯红,破口大骂,并且狠狠地把花儿铁的瘸腿掐了一把。
……
石坂屋
两间房
西边的太阳
穴居之城
附录:“底层”的艰辛与温暖——读赵光呜的《穴居之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