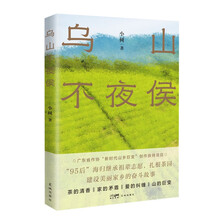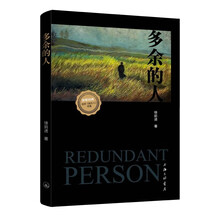铃声响起,她拎起了听筒,电话那头一阵沉浊的呼吸后,苍老的声音夹着不可抗拒的威严:“如果明天诺斯教授还活着,那么,你只有一条路可走——死!”摔听筒的声音似广漠空虚里的刀剑之声。她的手微微地抖,听筒从耳际掉到地下,纤白的五指滑到自己裸露的前胸,缓缓走到镜前,镜中的人裸露着脖颈,血管像一条条通向死亡的小路。
打开抽屉,将两支透明“死亡液体”放入口袋,带上武器和骷髅面具,出门,钻进自己的小车……车上,她想,教授每天都离不开葡萄酒,只要把“死亡液体”混入酒中或倒人饮水机里,那么,教授就绝不会活过明天中午。
将车停在阴阴的林木内,下车,浓浓的酷热扑面而来,月光下的约翰·霍普金斯医学院似一幅陈旧古老的黑白画,而树影下的小道更似一条通向地宫的森森之路。耳畔,风摇动着树叶,似是雨打芭蕉的声音,夹着无限恐怖撞击着她的耳膜。
轻轻踩着楼梯往上走,最后在四楼一扇门边停下,仔细地听着房间里面的动静,什么声音也没有,一片广漠的死寂。
把手放在了自己的胸口上,跳动的心脏似乎要穿出胸膛。看看四周无人,她将面具扣在头上,借助微弱的光线,将钥匙插入锁眼,门开之时,身体迅速隐人。‘关门的刹那,一束光线直刺她的双眼,弹丸之地顿时由漆黑变成光天化日。对于这种猝不及防的变故,她倒抽了一口凉气,两只瞳孔完全扩张,快速眨动着双眼以适应刺目的亮度,同时从腰间拔出贝雷塔手枪……然而,周围却是死一般寂静,既没有人声,也没有看见任何可怕的面孔,更没有发现任何对着她的武器。
立刻,她明白了,灯光是声控设置,是她的脚步声或是关门声点亮了墙壁上的聚光灯。
然而,她还是在心中暗叫不好,因为这灯安装得实在有点怪,难道是一种信息传感灯?曾经,她的同事就经历过这样一件事——灯亮之后,信息就传到主人手机上,主人报了警,警察从天而降……如果真是这样,诺斯教授的手机一定会告之他房间里进了不速之客,并马上警报,而她也将有可能被警察捕获。
恐惧深入骨髓,她想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关掉那炫目的聚光灯。然而,无论怎么寻找,就是找不到控制开关。看到桌上立的半瓶葡萄酒,她迅速从身上取出一支透明的液体,倒人瓶子,摇动,转身走到饮水机边,伸手去摘瓶盖,聚光灯突然熄灭。
恐惧从黑暗角落席卷而至,深深地渗进了她每一寸肌肤,但她还是将液体全部倒出。
转身正欲出门,突然又觉悟到什么,伸手摸到墙壁开关,大吊灯放出柔和各色光芒。她抬头扫一眼天花板,又不由得暗暗叫苦,因为两个摄像头,静静地看着她。
这样也就是说,她所有的动作全被记录下来了。
不想自己被暴露,去卧室找电脑,她想,只要把电脑内的硬盘拿走或者破坏,才能销毁证据,保护自己。
很快,电脑机箱内的硬盘就被她取到手中,突然,门外又高又尖的女生叫声像一把锋利的匕首划过空气,让她有瞬间被撕裂的感觉。她本能地捂着胸口,似是想阻止心脏从身体里逃出来……屏住呼吸,脚步声由远而近,推测有可能是来抓她的警察,她快速熄灭灯光,快步冲向窗台,拉开窗门,虽想跳下去,却是不敢,因为从四楼跳下,只有一种可能——粉身碎骨。
看看楼下黑森森的杂草,她将硬盘丢出窗口,右手紧握贝雷塔手枪,藏身落地窗帘之后。
门被轻轻打开,炫目的聚光灯再次将房间照得雪亮。进来的人不是警察,也不是诺斯教授,而是一个身穿紧束的夜行服、戴着红外夜视镜、身材像男人一样彪悍的女人。女人进门之后整理一下额前散落的头发,似乎并没有觉得房间有什么异样。只见她这儿翻翻,那儿找找,最后向卧室走来……步声虽轻,却似死神撞击着人类的死亡线,她在窗帘后紧握贝雷塔手枪,食指压着扳机,心想,如果受到威胁,那么只能先下手为强了……窗帘后,她尽量克制自己急促的呼吸,明显察觉到手心已沁出一层细细的汗。尽管,只要她的食指轻轻一压,“贝雷塔”就可以喷出夺命的火焰,但如果这样做,谋杀诺斯教授就会彻底失败,她便会受到上司残酷的惩罚。
卧室的灯被打开,女人踏进卧室,就在她决定扣动食指时,女人在电脑前坐下,伸手去开启电脑,见电脑没有反应,就去查线路,一连试了多次,最后恨恨敲了几下键盘,退出卧室。
她长长地缓了一口气,但马上又陷入无限的惊恐之中,因为她看到安妮正抓着桌上的酒瓶往杯子中倒酒。她心中暗骂:“这笨蛋女人,难道就没喝过葡萄酒?找死!要死也不能死在诺斯教授房间,坏了我的大事。”自知无力去阻止,心想,等她暴死之后,就把她拖人衣柜中,这样,且不更完美?
……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