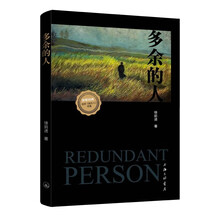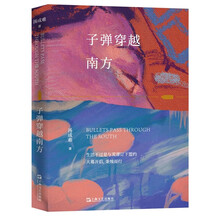如果在几年以前,你说句“一寸光阴一寸金”,像我父母一样在面前告诫我时间的珍贵,我可能会对你另眼相看。我的意思是说我会觉得你了不起,懂得一些人生的至理名言,或者拥有非凡阅历。回过头想想,我感到我那时的确幼稚得有些可笑。对于一个经历不幸,身处迷茫的人而言,你如何能看到时间有这般重要?也许太多时间只能使他陷入无穷回忆,让人愈发神经衰弱。想想可真是要命。所以你若下次见了我,最好提也别再提“一寸光阴一寸金”诸如此类的废话,更无须板着面孔对我说:“时间像奔腾的激流,它一去无返,毫不留恋。”
那个星期五清晨,我独自一人在学校的宿舍里,靠着窗台呼吸晨间的新鲜空气。夜里刚下过一场小雨,北京的晨空显得有些灰暗。远处成群的高楼矗立在天空下,一眼望不到头,忽隐忽现地笼罩在雾霭当中。风刮着近处的树叶轻微摆动,遮挡住树叶后的墙头和屋脊,给它们落上层朦胧的颜色。
我不得不承认昨晚失眠了,失眠总让人第二天看上去精神疲惫。假如昨夜雨下得不是那么时断时续,我想我也不必借助音乐最终人梦——淅淅沥沥的雨声通常就会让人产生困意的。于是我戴上了耳机,打开随身听,开始听我表哥前阵儿送我的一盘音乐带。我表哥叫苗苗,是个有前途的年轻人。他大学毕业后放弃了所学的法律专业,转行跟一个电影导演拍了电影,搞出些名堂,经常扛着摄像机游荡在世界各地。这盘音乐带是他今年早些时去泰国拍戏特意买给我的,是泰国当下一个流行女歌手的最新专辑。上上个星期天,我表哥突然在美国给我打电话,说他又有一个电影要开机了,是和美国的制片人合作拍摄的,完成后可能会在国际的大电影节获奖。“要知道,在这行想更好地生存,你就得时刻承受巨大压力,说不定哪天连裤衩都得脱下来给别人。”——表哥常说这样的话,所以听到这个鼓舞人的消息,我真替他感到高兴。
我就那么靠着窗台呼吸了一阵新鲜空气,把目光转向了操场。晨雾中的操场上,早起的学生和老师已经活动开身体了,有的在悠闲慢走,有的原地小跳放松,或者对着篮筐作投篮练习。我所在的学校比起北京其他高校来简直是小巫见大巫,简陋到了极致。面积不大的校园周围都是古老的近乎荒废的建筑物和高高的白杨树,这些建筑物建造于二十世纪四五十年代,除了风貌古朴外,几乎没有任何实用价值,以至于我表哥第一次来这地方做客时说,这儿原汁原味,很适合拍恐怖片。校园的南边是后来新修的食堂和教学楼,那也是二十年前的老古董了。从教学楼的后门出去,迎面有个占地约一百平方米的小花园,种着些常见的花草,正对着校园中心的图书馆和医院。再往北走就是这片堪称为学生唯一乐土的操场了,可惜操场面积也不大,三百米跑道转一圈到头,边上有个用铁丝护网围着的小网球场。就在这块狭小的空间里,每天的清晨与下午,依然充斥着各式各样的学生,从事着各式各样的活动。
校园的西侧有个小门,出去是教师宿舍和一些必要的基础设施。满足学生的日常所需。那边的小理发店男生剪头只要三块钱,不过总排满了顾客。我刚来学校报到时去过那里一次,她们给我发了张写着号码的纸片,让我按序等候。嘿,我在那里等了差不多两小时,最终才得以剪完。我很不习惯坐着理发时,旁边有群等候的陌生人对我品头论足,尽管他们的举动看上去很隐蔽!因此那次不愉快的经历之后,我再没光顾那家理发店。不远处的学校澡堂则在下午限时对公众开放,一个长相丑陋的老头负责开门、收票、打扫卫生。老头看上去很凶,不准男生在澡堂子里大声歌唱。有时我想,如果女生在二楼的澡堂也唱歌的话,他是否有上去制止的冲动?毕竟那个对男生来说可望而不可即的地方,只有他才有权出入——比比其他地方的看门人,给澡堂看门是个多体面的职业。
校园的东侧就是我所在的学生宿舍了,砖砌的红色小楼纵列成排,像一排排齐整的鸟笼把我们困在里面——我想告诉你的是,这是个妨碍人自由成长,压制人想象力的好场所。如果你不置身其中,了解不到我们的生活,就像你蛰居于这低矮的楼层里面,无法体会登高望远的心境一样。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