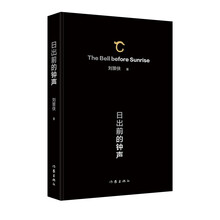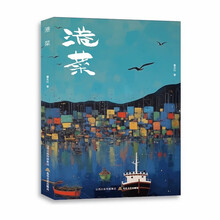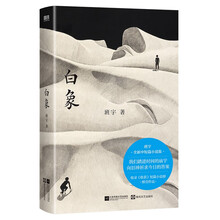田野上的积雪还没化净,又一场飚风搅雪,搅得满世界都是苍白和凄凉。
16岁的裘宇同,肩背书包佝偻着腰,像风雪中的枯叶,跌跌撞撞向长途汽车站赶去。他的额头已经微微见汗,端正的五官被饥饿洗濯得越发清秀,一双圆眼在浓眉下清澈明亮,忽闪一下,闪露出少年人少有的忧郁和坚强。这时的裘宇同饿得前心贴着后心,想直却直不起腰来。其实,他书包里有吃的,有四个馒头一个半窝头——胃口不断向大脑传递要吃的信号,他用顽强抵御食欲,宁肯把裤腰带再勒紧些,也要把这点吃的送回家,交给母亲。
裘宇同的家在滨海市近郊月牙河畔月牙村,是种菜为主的园田区。大城市城乡结合部的菜农比远郊及外县农民生活虽然好些,能凭粮本到粮店购买成品粮,但不掐着吃,家家户户每个月的定量吃不到半月就会盆干碗净米尽粮绝。
上月末的星期六,他回家拿过冬棉衣,发现母亲的两腿浮肿得像发面饽饽,手指一摁一个坑。就这样,吃饭时母亲也舍不得吃口净面饼子,只吃个菜团子,喝些菜粥。菜团子是一团烂菜滚上面醭,蒸熟了用手捧着吃。菜粥,是把白菜帮子、胡萝卜缨子切碎了,撒上一把棒子面熬成的,稀汤寡水灌大肚不解饱。
母亲的那份定量基本都省给了父亲。父亲常常被大队叫去出义务工。义务工是只干活不挣分,还得下大力气干又脏又累的活。干一天活已经筋疲力尽,夜晚还常常熬鹰似的交代问题。母亲怕父亲撇下老婆孩子去到另一个世界——紧挨月牙村的桥头大队四类分子伍福禄,不就是因为饿急了偷了两把喂牲口的豆饼渣,经受不住民兵黑白折腾跑到火车道卧轨自杀的吗?为此,母亲想尽办法让父亲吃好点,吃饱点。可她能想出什么办法呢?掐儿女们定量,舍不得,只有饿着自己。
裘宇同在离家六十多里的海沽中学住校上高一。学校怕住校生掌管不好自己的定量,就规定食堂每天发给住校生一斤粮票的饭食:早饭二两,一碗稀饭半个馒头,午饭四两,两个馒头或一碗籼米干饭,晚饭四两,两个窝头。早饭的菜是一块咸萝卜,午饭和晚饭的菜几乎一成不变,不是萝卜白菜就是白菜萝卜。菜里有盐有汤就是没油腥。没油腥的胃口像无底洞,吃多少也空落落的。裘宇同的肚子总叫,不是要吃饭了叫,是刚吃完就叫,根本没吃饱。他吃饭用不着单独刷碗,每次都是往饭后的碗里斟点开水,用筷子蘸水把粘在碗上的米粒汤汁洗净,把刷碗水喝进肚子。
在学校,裘宇同一想起母亲的浮肿,就难受得要哭,上课就有些走神,做作业就有点浮躁。他决心挤出点口粮,周末带回家,让母亲吃口净面馒头。
他从星期五开始做星期六回家的准备。星期五的早饭,那半个馒头他没舍得吃,只喝了一碗稀饭。稀饭是放碱熬的,虽然汁浓,米粒却有形无骨,悬浮在汤汁里,绝不沉底。说玄了,一眼能数出一碗稀饭里有多少个米粒。
中午饭的两个馒头他没吃,只吃了早晨那半个凉馒头。晚饭是食堂几天前剩的米饭,一则他饿得心慌,二则怕不好带回家,才全部吃掉。这样,星期五他省下了两个馒头。
星期六早晨,他又只喝了稀饭省下半个馒头。中午饭时,新发的两个馒头全都留着,只把那份旱萝卜菜冲汤就着早晨那半个凉馒头吃进肚子。下午下了第二节课就放学了,他拿饭卡到食堂领了两个窝头一份白菜。白菜就着半个窝头吃了,余下的一个半窝头装进了书包。心想,忍着点,坐上汽车用不了天黑就到家了,家里有菜团子菜粥……裘宇同的定量31斤,这是国家在节粮度荒的困难时期对中学生的格外关照。可是食堂发给住校生的主食分量明显不足:窝头眼大,馒头很暄,米饭黏糊。乍一看窝头不小,但皮薄得几乎透亮。二两一个的馒头用手一攥,一口就能吞进肚里。食堂大师傅不仅蒸窝头馒头的手艺高超,给学生盛米饭时也有绝活,他们常常把大拇指伸到盛饭的标准碗里,盛了米饭用刮板在碗口一刮,本该给一平碗饭,可碗里还有个大拇指“吃”空额。
那天,刚开过午饭,食堂朱师傅腰扎围裙,肩披棉袄,倒背的手被棉袄遮盖着,信步走出食堂。来到学校门口,裘宇同和几个同学从背后快步走来,走到朱师傅近前,一个同学推了裘宇同一把,裘宇同撞在朱师傅身上,朱师傅打个趔趄,饭盒离手,“当啷”一声掉在地上,炼油还没炼透的肥肉渣从饭盒里飞溅而出!朱师傅心慌,赶紧猫腰撅腚拾饭盒,没想到六个馒头从怀里滚落在地上。
这一下,炸了营!住校生们早就疑心大师傅往家偷吃的,纷纷向校长反映,食堂缺斤少两,炊事员中饱私囊。学校对食堂进行了整顿,整顿的结果是,炊事员们再往家里偷带东西更加小心更加隐蔽。
此后,每当开饭,学生们一进食堂就用筷子使劲敲碗,口中还念念有词:“稀饭稀,馒头小,窝头眼大干饭少,我们的定量哪去了?”赶到长途汽车站的时候,裘宇同愣了——雪太大,汽车停了。他摸摸书包里的干粮,决定步行回家。
冬季天短,加上阴天,下午四点多钟天就擦黑了。饿着肚子黑灯瞎火走六十多里雪路,对裘宇同来说,是个严峻的考验。看看昏黑的天空,想想母亲的浮肿,裘宇同默默发誓:就是走一宿,我也得让妈妈吃到我省下来的净面馒头!空肚子走在冰天雪地的黑夜里,裘宇同才真正懂得什么叫“饥寒交迫”。
沿着公路走了十多里地,裘宇同早已浑身是汗,是虚汗。他情不自禁地伸手摸了摸书包,真想吃个馒头,但不行,馒头是留给母亲的,怎么说自己在学校也能一周吃上三四次馒头,虽然不饱,可母亲最少半年没吃过白面了。要不,把那半个窝头吃了吧,犹豫一下,也不行,什么时候才能走到家?再坚持坚持,实在顶不住了再吃,他又忍住了。
走啊走,六十多里地怎么这么长啊!开始他还在村边公路上偶尔遇上一两个行人,可越走夜越深,越走越见不到人影。后来,连个喘气的活物都看不见了。
也许是肚子太饿,也许是惦念母亲,他心里空落落的就是不踏实。.深一脚浅一脚走着,实在累了,走不动了,只好靠在路边的一棵杨树下小憩。
刚坐下,东北风就从他脖颈钻到后心,飕飕的。被汗水浸湿的棉袄被风一吹,铁板似的贴在后背,寒彻筋骨。坐了一会儿,他想站起来继续赶路。
一起身,觉得眼前发黑,金星乱舞,赶紧又坐下。他知道这是连饿带累体力透支造成的,就把手伸进书包,先摸到那四个馒头,又摸到那一个半窝头,肚子立刻咕噜咕噜叫了起来。他狠狠心拿出那半个窝头,先用门牙咬了咬,没咬动,窝头已成冰疙瘩。他用后槽牙连咬带掰,一点一点地吃了起来。吃了几口,觉得口干,拨拉拨拉身边积雪,从中间抓了一把洁净的雪攥成球填进嘴里。窝头虽硬,吃到嘴里却又香又甜。他尽量放慢吃的速度,尽量享受吃的美感-,须臾之间,那半个窝头还是吃没了。
他突然有了一个奢望:要能敞开肚皮饱餐一顿刚出锅的窝头,然后躺在家里的热炕头上睡一觉,那可是人生最美最幸福的事了。
此时此地,此景此情,少年裘宇同苦笑一下,觉得自己可以跟志愿军战士媲美了:他们吃一勺炒面就一勺雪,我是一个雪球就一口冰凉棒硬的窝窝头。
他真想再吃一块窝头,哪j怕一小块,但想到母亲,立刻停住了。他站起身来,屁股上粘了好多雪,用手扑落几下,有的雪已经化成冰粘在裤上了。
快天亮的时候,筋疲力尽的裘宇同终于来到了自己的村子。就要见到母亲了,就要让母亲吃到自己带来的白面馒头了,就要听到母亲饱含爱抚的责备了:你这孩子,自己都饿晕了,还惦记着妈妈。但母亲那眼神一定全是夸奖,瞧,我小儿子多孝顺啊!孝心增加了力量,兴奋驱散了疲劳。他加快了脚步,向家门走去。
……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