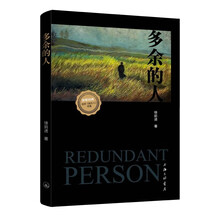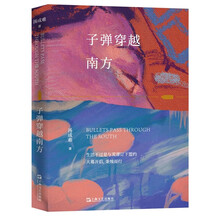上卷 黑暗中的眼睛
号子
关押我的地方是位于友谊西路的市公安局五处看守所。
薛林家的那个小巷也在友谊路上,离看守所很近,警车开了不到五分钟,便拐进一个警戒森严的大院。
检察官朱晓没有与我同行,后来我知道他是乘另一辆车到我家去“抄家”了。那个带队的矮个子警察将我带到一扇紧闭的黑色大铁门前,低声命令我:“喊报告班长。”
我抬头一看,大门上方是座方形的岗楼,岗楼上有个背枪的哨兵。大概那就是“班长”吧。
我心里正憋着一股气,看都没看那警察一眼,心想:又不是我主动申请到这儿来的,我喊什么报告?我今天就不喊,看你让不让我进去?
我没有喊报告班长,那扇黑铁门却自动缓缓地打开了。矮个子警察带我走进岗楼下的一间办公室后便给我卸了手铐。这副铐子在我手腕上停留了总共不到20分钟。
办完移交手续,警察一言不发,带着几个武警转身走了。
看守所办公室的灯已经亮了。办公室里只有两个人。一个身材高大粗壮的中年人上下打量了我一番,问:“你是哪里的?”
“报社的。”
“报社的?”他显然有些惊诧,“记者?有什么事吗?”
该怎么回答呢?说没事,没事你到这里来干啥?说有事,我犯啥事了?
我苦笑着摇了摇头。
坐在办公桌旁边的是位穿便装的年轻人,高个子警察问我时,他在填写登记表。当我报出我的名字时,年轻人猛然抬起头,皱着眉头看了我一眼,随即又低下头继续填写。
例行登记完毕,他们又来搜我的身,将搜出的记者证、钢笔、钱等物放到桌子上,又解下了我腰间的皮带。我不知道他们为什么要解我的腰带,大概是怕我借此物来悬梁吧?
我真想告诉他们:我是不会自杀的,爹娘生我养我不容易,天塌下来我也不会自寻短见,何况天也不会塌下来。
我只好用手帕系住裤鼻儿。真有些斯文扫地的狼狈!
进来一位女警察,看样子是保管员。她将我的东西清点后填写了“在押人犯存物清单”,随手从中抽出十五元钱,说:“多带点儿,免得三天两头地取。”
那穿便衣的年轻人站起来,说了声“走”,便带我走出办公室。
这是高墙内一条长长的巷道,两边是一排排的监房,每一排都是一个独立的小院。暮霭沉沉,巷上吹着料峭的寒风。我在寒风重暮中走向牢房。
“为啥事把你抓来了?”年轻人边走边问我,声音低低的,似有淡淡的忧郁。
见他没有穿警服,我猜想他可能不是警察,心里便多了点儿亲近感,说:“现在我也说不清。他们调查时,说我在汪剑康商店买了辆摩托车,是受贿……”
“唉……”年轻人叹了口气,苦笑着说,“现在的事,难说。”
他将我引到监所的最后一排,对门口站着的一位穿警服的老警察说:“报社记者,写过不少文章呢!”说完就走了。
后来我知道,这年轻人叫黎立强,是在看守所服刑的犯人。由于第一次接触中他对我的同情与关照,我们成了朋友。
那管理员有五十出头,面色很黑,说一口浓重的关中方言。他带我走进管教室,让我在一个状如腰鼓的石凳上坐下,开始询问我的姓名、单位、籍贯、年龄。他在填写人犯登记卡。当他问到我犯了什么罪时,我说:“不知道。我没有罪。”
黑脸老头并没有动气,也没有和我理论,他停下笔,温和地问:“那是咋回事?”
直到这时,我那压抑在胸的怒气才开始喷发,我气呼呼地说:“我在汪剑康的商店买了辆摩托车,当时钱不凑手,汪剑康让我打了张欠条。这欠条检察院也见了,白纸黑字,就这么点屁事,调查了半年多,今天又兴师动众地把我抓到这儿来。还讲不讲理?还有没有王法?”
说到激动处,我手臂挥动,根本忘了这是在监狱,我是在和警察对话。
那老头却不动声色,沉思了片刻,似乎是在斟词酌句,然后才缓缓地说道:“你也别激动,案子的事,外面自会调查处理。你要相信法律。啥叫既来之则安之?到这里来了就守这的规矩,是吧?你是知识分子,道理我就不讲了,是班门弄斧喀!好吧?”
老头的温和谦恭倒让我有些不好意思了,火气也消了,我说:“这一点,请管理员放心,我就是有天大冤枉,也不会在这里跟你们过不去。”这话,很有点儿江湖味儿。
“那就好。”老警察站起来,“你放心,我们也绝不会把你按一般盲流对待的。”说着从桌上拎起一串“哗哗”响的钥匙,朝门外走去。
老警察忽然又像想起了什么,拧过身问我:“你到报社前是干啥的?”
在工厂当工人。”
“好。”他小声地说,“进号子后不要说你是记者。号子里很复杂,就说你是工人就行了。有啥事跟外面说。”(以后我知道,“外面”是这位老管教的习惯用语,他把号子以外的人都说成是“外面”,包括他自己。)
这一排有六间号子,全是砖木结构的老式房子。早就听说过,这看守所在解放前就是座监狱,关押过不少共产党人。而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这里也关押过不少在运动中被“揪”出来的大人物。地下党员出身的市公安局第一任局长就曾在这儿被关过十几年。
老警察打开第二间号子——先开锁,后拉铁门闩,我头也不回地走了进去。
“咣……当”,号门从外面闩上了。
这是一个春天的黄昏,我走进了过去只是在电影、电视上见到过的牢房……
我斜依在号子的门上,冷冷地打量着我的“新家”。
这号房有十五六平米,进门是条窄窄的走道,不足一米宽;走道尽头的墙角竖着一个一米多高的小便池(后来知道号子里称这为“毛驴儿”)。除了这些,整个房子便是一排两头挨墙的大通铺了。叠起的被褥摞铺的最顶头,光溜溜的硬板床上站着十几条汉子。我进来时,他们还在床上来回走动,像逛街;我一进门,他们便停下了,目光齐刷刷投向我。我靠门框站了大约两分钟。这两分钟,没有人搭话。我双手插在裤兜里,毛料中山装敞开着,脸绷得紧紧的……这架势,大概真的把这伙盲流唬住了。
唬住了别人,却唬不了自己。我知道我现在已经沦落到“与狼为伍”的地步了。从现在起我将在这里与这伙盲流们日夜厮守,同吃同住同受苦,作家的风光不再,记者的冠冕落地,我是这里的囚徒……轻轻叹了口气,我在靠着牢门的一块床板上坐下来,习惯性地伸手向衣兜里摸烟。没有,烟火早在入狱登记时就被没收了,前、后的管理员都交待过我:号子里不准抽烟。
这时,有人搭话了,声音怯怯地:“这位老叔吔,你……是啥事嘛?”
我扭过头去,见身后站着一个穿蓝色大裆裤的小伙,年纪顶大不超过二十岁,长得眉清目秀却又一脸的油滑气。此刻,他身子弯着,歪着小平头望着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