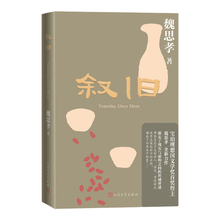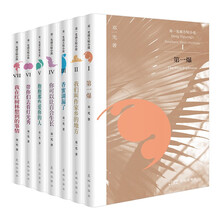1 1979年底。
还只有二十五六岁的杨元朝,准时来到市公安局政治部干部科报到。
他是北京人,由于家庭的变故,此番调内地公干纯属无奈之举,心不舒,气不爽,心不甘,情不愿,硬着头皮不得已而为之。
接待他的是干部科李科长,虽然年及半百,但依旧精神头十足,给人以精明强干不服老,革命人永远年轻的印象。
李科长从事干部工作多年,作为前任大军区领导的夫人,对于干部子弟,一向很照顾,有一份天然的亲近感。
“你是杨元朝吧?欢迎,欢迎。”李科长像是招待远方亲戚似的,满面春风地招呼着。
杨元朝谦逊地笑笑,恭恭敬敬地把一个大牛皮纸信封袋递到李科长手里,说:“这是我的调动手续,请您查收。” “快坐,别客气。今后,你就是我们市局的人了,一家人不说两家话嘛。” 李科长一边笑容可掬地说着官话、套话,一边手脚麻利儿地打开信封袋,从里面抽出调动手续看。
早在半月前,李科长就已经知道有一个颇有来头,叫杨元朝的军干子弟由北京调来,相继给她打招呼的人里,既有省厅和市局的主要领导同志,也有已经离职休养的丈夫,均郑重地叮嘱她,接待要客气,不许拿出惯常干部部门的老套作风——居高临下,颐指气使,免得伤害人家从北京调来的小字辈儿。
尽管她素来认同军队大院儿的孩子,但却始终对于杨元朝的到来心存疑惑,为什么这个身在北京,老子又是军队要职的军干子弟,非要到我们梦城来呢?而且,还指名道姓非要到刑侦处公干不可?这里面到底有啥原因?他杨元朝又是出于什么目的和动机呢? 单从工作性质上来说,业内人都知道,刑侦处可不是好玩的地方,专门办大案子,如纵火决堤、强奸杀人、抢劫盗窃以及走私贩毒等,平时接触的人形形色色,三教九流,鱼龙混杂,还经常与穷凶极恶的歹徒短兵相接,刀光血影,出生入死,玩命的干活,属于警察行当里最危险的勾当。
俗话说,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可这个年轻人为什么放着好地方不待,偏要离乡背井到外地工作,而且挑最危险的工作呢?不由人不心存疑窦。
老于世故的李科长把目光从调动材料上移开,冲一直没有坐下,仍身板笔直地站在自己面前,保持着军人作风的杨元朝和颜悦色地说:“那行,手续齐全,我现在就亲自带你去刑侦处报到。” 刑侦处并不在市局机关大院儿里,由于系一线作战单位,自有其特殊的独立性,操练习武、外带射击,是家常便饭;再有,刑事警察成堆的地界儿,无论是武器装备,还是研究案子、审讯罪犯等,都需要严格保密,尽量不受外界的干扰,所以,必须得有一个地方单独办公才妥当。
“咱们走走吧,反正,刑侦处离得不远,顶多也就是一刻钟。”阿姨辈的李科长显得和蔼可亲,“不怕你笑话,到了我们这把年纪,就喜欢多走路,少坐车,一来呢,可以强身健体,活动筋骨;二来嘛,多做一些有氧运动,也有助于增加心肺的功能。总之,好处很多哩。” “是,”小字辈儿的杨元朝知趣地顺杆爬,“上年纪的人应该多活动,俗话说,生命在于运动。老从脚上来,腿脚利索了,才能长命百岁。” “你还挺会说话,很成熟嘛。”李科长心情不错地看了杨元朝一眼。
正逢上班时间,大街上已然是车水马龙、人流如潮,铃声、喇叭声混合在一起,显得喧嚣而嘈杂。
对于这个高大英俊的年轻人,尽管对他的来意不明,但打从一照面儿起,长期做人事工作、阅人无数的李科长就下意识地喜欢上了。她觉得,这个年轻人的身上,既有同是军队大院儿人的那种天然的归属亲近之感,说话也是够讨人喜欢,并且,长得够帅气,身高足有1.80米以上,腰板笔直,肩宽腰细,罩一身合适的蓝色警服,那叫一个精神,举手投足风度潇洒。一句话,就是看顺眼了。
一路上,李科长出于好奇和不解,不断拐弯抹角地打听起年轻人的最终来意:“小杨啊,我曾看过你的档案,表现一直不赖嘛。在部队时,立过功,受过奖,还上过两年工农兵大学。转业分配到北京市局以后,工作也干得挺好。
为什么你非要来我们梦省呢?而且,还非点名一定要去刑侦处干不可?你就那么喜欢当刑警呀?每天和形形色色的犯罪分子打交道,觉着冒险和刺激,是不是?” 听话听音儿,锣鼓听声儿,杨元朝明白,这位阿姨辈的干部科长是在质疑自己呢。不过,他不能把原因说出来,因为这件事让他羞于启齿,整个家门之大不幸。
他是聪明人,同时也是自尊心强的人,不想无辜受家庭变故的牵累,因此,便开始发挥能说会道的特长,做出一副推心置腹的真诚的样子,说: “首先,是为了陪父母,他们二老都已经老了,均已六十开外,接近古稀之年了,身体也不好,身边又没子女陪着,当子女的不能鞍前马后、端汤倒水地侍候尽孝,不应该;至于说想去刑侦处工作,那是我的最爱,您不知道,打小我就喜欢玩警察抓小偷的游戏,特别崇拜那些为民除害的大侦探和大英雄,所以,一转业便首选公安局;再说,我又在北京市局干了两年多,多少打下了一定基础,舍不得放下,既然调梦城来陪父母,当然最好还是干老本行,接茬儿当咱的刑警,这样,既不浪费资源,也能尽子女的义务,两全其美不是? ” “你倒挺孝顺,考虑问题也还周全。”见他理由充分,李科长虽不相信他的“穷白话儿”,但也不好再问。
为了彻底打消这个对自己未来命运可能产生重要影响的长辈的疑虑,杨元朝把事先早已想好的托辞进一步展开,抡圆了侃,套近乎:“阿姨,其实,您最应该理解我,因为,您也是军队大院儿的人嘛。打小,我就是你们这些阿姨看着长大的。我不是不喜欢北京,可我父母的情况和别人不同,自从我父亲调任梦城以后,身体每况愈下,病越来越多,还都是心脑血管方面的,动不动就犯病,已经抢救过好几回了。我妈也因在“文革”中遭受造反派的迫害,不幸摔断了腿,落下终身残疾,常年靠轮椅代步,活得更不容易。您说,他们身边,没个可靠人陪着行吗?起码,在精神上和老人的心理上,我们做小字辈儿的总该给老人一份慰藉吧?这也是人之常情嘛。” 听他这样振振有辞地解释,李科长不禁被他的一份孝心所打动,连连点头道:“是啊是啊,你们当小字辈儿的能这么考虑问题,够成熟,够懂事。如果每一个干部家庭的孩子都能像你这么考虑问题,就好喽。你想想看,这些年来,相当一部分干部子女闹腾得还嫌不够呀?由于不懂事,仗着有权有势的老子为所欲为,好高骛远,眼高手低,办了多少让人头疼的馊事?不仅断送了他自己,连带家庭也受影响,免不了跟着受连累背黑锅……咱们同病相怜,我家老头子的身体也不好,总闹病,吓得我时常心惊肉跳的,平时连觉都睡不踏实,唉。” 杨元朝接道:“这不结啦?百善孝为先嘛,做人就得知恩图报,何况是对自己的亲人和长辈呢?您说是不是这码事儿?” 李科长扭脸看着身边这个高大英俊的年轻后生,白净而松垮的脸上堆起更多的喜悦的纹线:“不赖,你让我喜欢上你了,就为你的这份懂事和孝心。行,年轻人,有志气,好好干吧。毛主席说过,你们是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未来一定是属于你们年轻人的。” “阿姨,我都已经二十五六岁了,算不上冉冉升起的朝阳,眼瞅着,已经快到晌午时了。”杨元朝有意玩笑,有意进一步融洽关系,套瓷。
“咳,你误解了,他老人家的意思是说,你们年轻人朝气蓬勃,可塑性强,经过努力奋斗,前程一定远大,并不真的就是说早晨还是中午,不过是一种形容和比喻罢了,你可真幽默。”李科长乐呵呵地说。
……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