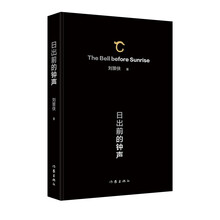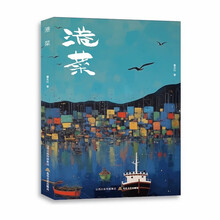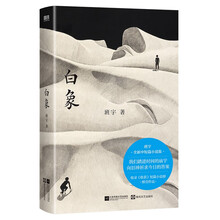黄大从冰窖回来,才知道娘叫洋人奸了。
黄大的冰窖在大沽炮台脚下,在白河的河汉。河汊像裤脚,一脚伸向白河,一脚伸向大海。炮台像男人裆下的卵子,凸着,圆圆的。热烘烘地饱满。
黄大从冰窖出来,一时间,老了上百岁,像一棵朽了的枯树,白怏怏地僵着哩。
黄大恍惚记得,日光一蹿一蹿,蹿出海面,蹿到三丈船桅的时候,海上一通炮响,放出一团一团的火球。火球在日光下,绛紫血红地飞。火球落地,东也爆炸,西也起火。林子、芦苇、黄蓿、蒿草一眨眼由绿变黄,由黄变黑。一世界乌鸦、麻雀、飞鸟把大沽口上空遮黑了。
黄大闹不明白,光天化日咋响炮呢?黄大从小没离开过大沽口,天外的事情他咋能想到呢?
咸丰六年。美、英、法三国发出修约照会,企图修改《南京条约》,遭到清政府拒绝。英军开始行动,3天之内连占虎门各炮台,接着攻陷了广州城。
咸丰八年,三国公使决定集结军舰,北上天津。
4月中旬抵达白河口,照会清政府,限6日内派全权大臣谈判。直隶总督谭廷襄奉旨斡旋。
5月20日,英法联军舰队向大沽口炮台开炮,气焰嚣张,叫嚣要踏平大沽口炮台,打进北京城。
黄大记得,第一颗炮弹,悠地一声,从冰窖上空飞过,就有一团火球落在了冰窖的洞口。
火球翻花滚浪,掀飞了冰窖洞口的半块草帘子,草帘子的三股麻绳像爆竹的引线,哧溜哧溜就燃着了,火星子成串,遥遥地蹿上天。就有了狰狞的爆裂声。
一股浓烟,裹挟一股血气,扑进冰窖,冰窖顿时黑了,伸手不见指,盲人一样的黑。
冰块上,密密麻麻落了一层灰,像五黄六月落黑雪。黄大惊奇地用手指在冰上一抹,放在鼻下闻闻,一股甜丝丝、辣丝丝焦煳的味儿,蹿到了嗓子眼儿,黄大一个喷嚏带出一个屁。
黄大惊天动地干咳了。
炮不断地响,火球不断地在冰窖上空红艳艳地绽放。火球一飞,起了风一样的唿哨。火球落地很沉,爆裂得很响,好似隆隆的雷声,嗡嗡震的耳鸣。
冰窖里一明一灭,一灭一明,像闪电,把黄大通身抹黑划亮。石子、土块欢蹦乱跳着飞进来,砸在冰上,打在脸上,黄大土头灰脸地萎缩了。
咋漫天遍野都是火球?火球咋那么大的劲头儿?火球腾空开花的时候,像生出了无数七扭八歪的手,把云彩撕得跟裂布一样,刺啦刺啦地响,又像抬腿在膝上撅烧柴,嘎巴嘎巴,一截~截把天爷的筋骨肋条撅折了。
黄大蹲在冰窖排水的水道上,抱着头,一步一步往冰窖深处蹭,就有浓烈的血气味、火药味,~股一股朝他身上扑。扑上来,拧着劲地往他的鼻子眼儿里钻,往骨头缝里扎,往脾胃里拧,拧得黄大恓恓惶惶。
两时一刻,南北两个炮台,一下就荒了,像一阵大风刮过,把炮台掀翻,成了一堆废土。
炮台上,飘着丝丝缕缕的青烟,像清明坟茔上连绵不断的香火,南北炮台勾连的整个小镇,和小镇周遭的坑洼荒野,一时间,像亡人,绝了气息。
下晌,炮不响了。
天地才真真正正地肃静了,坟茔一样的肃静。
黄大蹭到冰窖的洞口,间或听到,从海边漫过来响动。响动杂乱,从他的头顶漫过一层又漫过一层。
黄大在冰窖洞口的缝间,看见,夕阳下,排排缕缕的洋人肩着大枪,大摇大摆,得意的哇哇地狂叫,遥遥远远地往西边漫去。
黄大听不懂叫的啥?哇啦哇啦的,像一坑的蛤蟆。有人举着白地儿红色交叉的米字旗,有人举着蓝白红三色旗,在头顶上使劲地挥舞,舞得天红一片蓝一片。还有人牛嗥一样,呜啦呜啦地唱歌,得意洋洋地端着枪,把枪夹在裆下,屈着腿,双手像攥着卵子,滋尿一样,直对着太阳落下的方向,自由自在地喷出了血红,发出了肆无忌惮的脆响。
枪声伴着歌声,在大沽口地界悠悠扬扬。
悠扬遥远,四处便是奇妙而古怪地肃穆。
太阳丝丝缕缕抖到了西天,西边的天空失了血气,悄然成了橘黄色,像一页寡淡的草纸,薄薄的,沙沙啦啦地落到白河里,河水把橘黄一层一层地洇湿,轰轰烈烈地淹没了。
黄大悄悄地从冰窖出来,腰杆渐渐挺直,挺直了就四下嘹望,他看见了卵子一样的炮台上,立着一个黑影。
黑影朝向大海,在炮台上迎风立着,粗布白衫被海风扬起,猎猎抖动。
……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