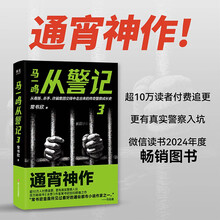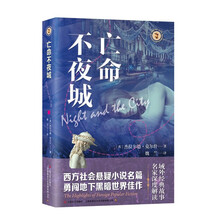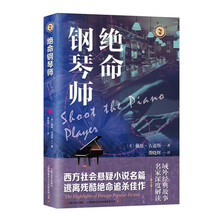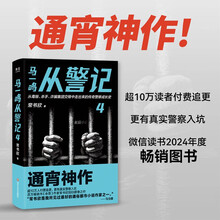写上面那一大坨文字差点累死我。也许我是一个基本合格的故事讲述者,能把很多原本无聊的事情说得妙趣横生,可描述场景不是我的强项,完全不是。<br> 所以接下来,我会选择我最擅长的方式讲述这个故事,努力让其中所有的沉重都变得轻松。<br> 先把白梅的死放在一边,咱们继续讲我和白兰的故事,还有那个丁子光。<br> 说老实话,时隔多年之后,如果没有照片,我几乎无法准确描述出白兰的外貌。很多时候,她更像一枚轮廓清晰内容模糊的剪影,夹在一堆乱七八糟我无暇也不愿翻找的回忆之中。<br> 但我始终无法彻底遗忘她,在一些莫名其妙的时间和场景中,她总能从我记忆深处缓缓走来。这几乎成为一种习惯,就像在这个故事的很多片段中,她会不经意地出现。<br> 其实她只是个配角,或者说一张布景。<br> 我的钱包里曾经有张白兰的照片,她是个挺好看的姑娘。<br> 那年夏天我得了点小毛病在市人民医院度假,认识了白兰。当时她是内科的实习大夫,皮肤白皙,文静纤弱,脸上总挂着近乎羞涩的微笑。<br> 后来我发现,她也跟很多女孩子一样,有点刁蛮和任性,就像一杯醇厚昂贵的陈年白兰地,喝到最后才发觉杯底的冰块有杂质,欲罢不能于心不忍。<br> 第一眼见到她,我心里就觉得毛茸茸的,像是长了草。那个时候我青春年少,勇于单刀直人地追求一切我认为美好的东西,结果碰了一鼻子灰。<br> 这事说起来其实挺没劲的。<br> 一个朋友来医院看我,拎着乱七八糟一堆吃的。我在病房里偷着抽烟,他给我削苹果兼把风,有点分神,被白兰抓了个现行。我臊眉搭眼地挨了顿训,我那朋友在旁边一声不吭,等白兰训累了把手里的苹果递给她,目光炯炯地问,你是不是白梅的妹妹啊,我是她同事,见过你的照片。<br> 再后来的故事比较恶俗,出院前我厚颜无耻地索要了白兰的传呼机号,然后就开始发春。连送花那么恶心的事都干过,诸般行径之浅薄恶劣,现在想起来恨不得一脑袋扎马桶里把自己淹死。<br> 白兰始终和我若即若离。后来我知道,她怕直接拒绝,会刺激得我悲愤难当投河自尽。我那会儿说话办事都直来直去的确有点缺心眼儿,可真没傻到那个地步。<br> 可惜白兰不知道,她看人总是不靠谱。<br> 有一天我赶在下班前去她单位门口伪造邂逅现场,靠着车门抽了两根烟,然后看到白兰从马路对面医院大门里出来了。<br> 背后的夕阳给她的身体镶了一道金边,白色纱裙长长的裙摆被风吹着轻轻飘扬,垂在身前的左手拎着白色帆布手袋。美得令人发指,是吧。<br> 很不幸,她还有只右手,而且也没闲着,正被我那倒霉朋友抓着,俩人笑得满脸都是褶子,你要非说那就是传说中的笑靥如花,我也不拦着。<br> 反正我当时欲哭无泪,恨不得冲上去掐死谁。<br> 那个年代大家都很含蓄,知冷知热也懂得廉耻,所以后来我谁也没掐死,老老实实开始了一段忧伤单恋,纯洁得让我脸红。<br> 我的那个朋友就是丁子光,大家都叫他小丁。时隔多年,我犹能记起他那张斯文儒雅的脸,戴着一副眼镜。<br> 后来,我和小丁都在感情上伤害了白兰,相互交织相互映衬像是一场比赛。<br> 如果一定要比较一下程度,我认为,不相上下。<br> 我和小丁认识得很早。<br> 那年我刚从警院毕业,到市局报到后,暂时被留在政治处打杂。<br> 大家不要误会,这个政治处跟香港警方那个政治部完全不是一个概念,人家负责的是监控弹丸之地乱七八糟多如牛毛的各方面情报人员,现在还肩负反恐的重任。<br> 咱们的政治处,负责全局所有干警的思想政治教育和相关管理工作。编印无数的学习材料,按年度对所有人员进行政治考评,基本上就是没事给自己找事。当然,偶尔也对一些出了问题的同志进行调查,拟定处分结论。<br> 据说政治处的权力还是很大的,干警的人事升迁必须得到他们的认可。可惜我在政治处那会儿负责的主要工作是扫地打开水整理陈年档案。<br> 所幸那段时间不长,很快我就满怀激情投入到一项当时认为牛B得一塌糊涂的工作中了。说来话长。<br> 那年夏天,市里出了个案子,大案,由省厅一把手亲自督办,成立了专案组。案件的宗旨只有两个字:打黑。<br> 由于一些没办法明说的原因,专案组的成员基本上都是从外地调来的。我是个例外,因为他们需要一个熟悉当地情况又年轻力壮的家伙做司机兼市内向导。<br> 案子办得很顺利,因为之前已经掌握了不少情况。还没入冬,那个倒霉团伙的几个主犯就全部到案了。接下来的工作变得很烦琐,收集材料补充证据。<br> 为了把这个案子办成无法翻身的铁案,本着打翻在地再踏上一万只脚的宗旨,在检察院的授意下,专案组除了进一步收集整理刑事犯罪方面的资料,又向税务部门求援,清查该团伙首脑开办的若干家公司的账目。<br> 税务局派来了几个稽查高手,其中就有小丁。<br> ……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