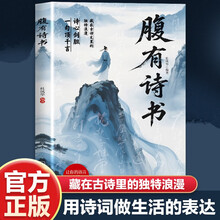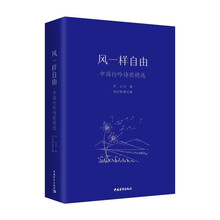每个人心里都有一个魔鬼
不要对我龇牙咧嘴
眼放绿光
我回避你并非因为
害怕,而是怜悯你终于不可避免地
沦落为兽,成为魔鬼的坐骑
你的威风是多么可怜可笑和可憎
如果我拧开灵魂的瓶盖
也可以放出一个魔鬼
更加凶猛的魔鬼
但在魔鬼的利爪下
都是伤痕累累的命运
我不拧开瓶盖,我逃避
是因为我目睹了太多
欲望的洪水中漂浮的腐尸和朽梦
如果你没有降魔的法力
请拧紧灵魂的盖子
造句
许多年前的小学语文课上
老师布置用“一……就……”造句
小美轻描淡写
“我一吃完饭就去玩了”
小美的孪生妹妹小丽
偷看了姐姐的作业本
这样写道:
“我一吃完饭就完了”
因此
小美嘲笑了小丽许多年
直到小丽
给小美现在任校长的这所小学捐款
造了一幢漂亮的教学楼
造句的故事
才宣告结束
小美校长还特别叮嘱
以后谁都不许再讲
这个故事了
春暖花开
春暖花开
应该干点什么了
先打扫房间
在不算破烂的木床下
扫出
写在白沙烟盒上的情诗一首
废弃的避孕套两只
未写完的求职信三封
硬币数枚
还有无头无尾的一段文字——
“这样的故事
只应该发生在梦中”
没有时间感受伤痛
小美春天买了一辆蓝鸟
小强夏天添了一部奥迪
小饭秋天住进了香蜜湖的高尚社区
冬天老曹和阿文在老家都做了单位领导
冬天我和阿丁、小林走在深南大道上
阿丁脸色发青
昨天相恋十年的女友因为他
在深圳买不起房子
回了湖南老家
他在湘菜王喝闷酒喝得
直接进了北大医院打点滴
醒来后只骂了一声:狗日的深圳
小林大病初愈
脸上还呈菜色
我的贸易公司刚刚关门
好心情也因此关了门
我们强打精神
走在匆匆忙忙的人流中
我们准备联手再搏一次
我们红着眼恶狠狠地说
如果这次再不成功
就和那个永远都抵达不了的远方
从地王大厦的顶层
跳下来
开三朵红花
哼,我们总要给深圳一点颜色看看
把自己想象成一个病重的人
把自己想象成一个病重的人
这样就可以停下来
抚摸一下伤痕
整理一下心情
清除一些垃圾
卸下垒满心中的石头
让我穿上蓝条的病号衫
在洁白的环境里走动走动
让我清洁地面对世界
多么轻松几只鸟
飞过山巅
山顶的积雪化为快乐的泪水
天空瓦蓝白云祥和
爱我的人和我爱的人
在我的病床前
来回走动
他们的脚步多么轻啊
总有一些人要离开你
走了那么远的路
才发觉
路,有时并不在脚下
才发觉自己
有时像个演员
像坐在舞台中央
热闹是别人的
自己只是一个
人戏太深的演员
才发觉,生活就是导演
你的离去
只是一个片断
而我的表演十分笨拙
我的痛苦一望无际
只是,表演还要继续
其时
未开声
已怆然
我再次写到远方
我再次写到远方,因为
到了深夜我仍无法入睡。我写到远方
一片白色的小药丸是否会告诉我
黑夜的深处,通俗地说就是
后半夜或黎明前,它们是否
就是黑夜的远方,我睁着眼睛
看着太阳升起,没有一丁点儿欢乐
黑夜似乎也没有一丁点儿快乐
白昼的远方不还是漫漫黑夜吗
我布满血丝的眼睛里没有一点晨光
我的远方在露珠里发出空洞的回响
我被黑夜燃烧
小小的欢乐被燃为灰烬
小小的药片放着幽微的光
似乎在说:“我就是远方”
想飞
想飞,飞出八小时以内的工作和冥想
飞出八小时以外的酒精、脂粉和空虚
飞出早餐、中餐和晚餐时间
飞出午后的倦意和灵感
飞出下午五点钟的钟声及其回响
飞出半夜的梦魇和冷汗
飞出灰暗的躯壳,这沾染无数恶习的臭皮囊
飞出恶俗的尘世,这宇宙间最大最黑暗的监狱
想飞,在我跛足的语言上飞
在笨拙的语法和修辞上飞
在黑暗的想象上面飞
在山风林涛的鼻息中飞
在麦秸、草垛和衰草的鼾声中飞
在四月的泥泞和雨声中飞
在岩石般冷峻的面孔上面飞
在神赐的静谧里飞
坐在椅子上面飞
趴在白纸上面飞
飞向未知……
走神
我非常不好意思地告诉你,我现在
不单单是在平凡的日子里,对着某个背影走神
我还经常莫名其妙地走神
中午去厕所时,拐进了同事的办公室
傻笑了一下,摇摇头,苦笑
下午去大良途经容桂拜访一个客户
却坐在了顺峰山庄的包厢里
在等人的过程中发呆,去了一趟厕所
晚上回到家里,想起未拜访的客户,又傻了。
换裤子的时候,发现牛仔裤的拉链洞开,更傻。
分散的注意力,让我的头顶堆满了初雪
我的青春、爱情、事业、朋友和隐痛
从四面八方涌过来,又退回
我疲倦地看着它们来来回回
昏昏欲睡,仿佛穿越了时间的孤独
花瓶
我失手打碎了
你最喜欢的那只花瓶
从此一朵花的惊叫
常在半夜把我吓醒
我千方百计弄来了
一只一模一样的花瓶
我看见你眼睛里
掠过的惊喜,像一朵重新绽开的花朵
再次见到这只花瓶时
它却蒙上了厚厚的灰尘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