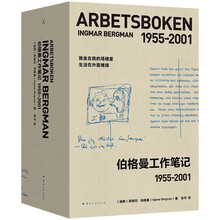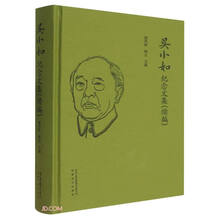情书
你也令我痴痴醉
亲爱的克莱德,
我一向不羡慕任何人。我不羡慕比我更有才分的人,看得眼热也有,但知道不是自己的。冷静后,还是写自己的字去。我不羡慕长得比我好的人。十九岁的时候痛恨过自己的平庸形貌,向老天请求能否收走我一点点才华给我一双笔直长腿或者迷人大眼。后来发现还是算了,我的眼睛努力睁一睁还是可以混珠的。(其实算蛮小的,我以前戴隐形眼镜总是很吃力,后来只好去买直径比较小的。)
这些是玩笑话。老实说,不羡慕任何人,是因为窥见过光鲜后的落寞,光环下的阴影。我的一个女老师,是我见过最成功的年轻女人,可是你要知道她那个压力、她那个累!她跟我说,一个夜晚,她坐在马路牙子上哭起来,不知道生活为什么是这样子。太不容易了。去年是我最顺利的一年,我的写作事业像一条笔直的直线一样向上冲,可是我选择了离开北京,去南京休整半年。我想那种繁重而成功的生活大概不是我现在想要的,我并不羡慕。于是推掉一些活计,离开一个环境,去养身子,养心。所幸上天很厚待我,在南京所发生的一切都那么意想不到火花四射,把我的生活塞得满满的。现在想起来,真的很怀念我丹凤街的小房子,怀念我阳台上的柠檬草、窗台的风铃,怀念那段清静碧绿又生机盎然的日子。
我只羡慕一个人。你知道的,我的好朋友琥珀腰。我羡慕她有一个那么好的男朋友。高中同学,一直恋到大学。家里都知道了,处得甚好。男孩子是我见过最好的一个,挺拔、高大、端正、不卑不亢、一直微笑、说话有见地,品位也好,也肯出力帮忙,价值观光明正确。这些都和她一样,所以是一对好人儿。我特喜欢和他们在一起,请他们吃饭也乐意。谁不愿意看见幸福的人呢?有一两次,吃完饭,她穿外套,他就自自然然地拿起围巾,替她围上,再亲爱地打一个结。还有一次,看电影出来,她的鞋带松脱了,他就弯下身子,跪下去给她扣鞋带。我在一旁看得做声不得,痴了过去。
羡慕。
少年情侣老来夫妻。是我最不能见,最不忍见的人。以前最讨厌看见情侣在公众场合亲热调笑,觉得忒没素质。可是我们在机场接吻那么自然,并不为了炫耀。知道自己是眼热,是心绪坏了,是羡慕。羡慕总也总也轮不到,得不到。我是羡慕那些平凡的幸福的。爱不能总置于绝壁之上,我知道,因为,太高了。
有时,我再三说服自己,我们爱得无与伦比,可是,仍旧不能尽数驱遣我的寂寞,比如此刻。我不能升腾我的情绪,像我们在一起的许许多多时候,那多么容易,兴高采烈或者柔情蜜意。可是我现在低落着。亲爱的,我不想回避。
或者,真的痛苦才驱使我拿起笔。前半个月分分钟只想待在电话旁边,说也说不完的话,笑也笑不完的笑。也有误解和曲解的时候,我们像陷在巨大语言迷宫里徒劳摸索,我们都气闷、无奈,讨论到口干舌燥、筋疲力尽。但都没有怀疑过彼此的爱,不会因为自己的失望和受伤挫败就去恶意地攻击另一个人。我们就是疼痛的时候也急切地想护住对方,顾惜不了自己。这总使我又难过,又感动。
升华。每一次的痛,每一回的闹,最后总是升华,能升华到更高。倾心相处,我们能。亲爱的,这多么好啊。如果是造化,我感谢;如果是我们本身能量如此,就能彼此激荡,我庆幸。
我,依旧和第一天一样,全心全意地感激能够爱上你,被你所爱,在爱上你的同时被你所爱。永不后悔。
现在,又是我自己了。虽然你说我们一直在一起。可是我真的有点感觉不到,有点沮丧。晚上去跟父母吃饭,谢谢那个让丈夫在日本给我买到安娜苏的阿姨--一家三口,很普通的,席间说起的,也不过是小孩子脸上的皮肤不好,总是有红斑,诸如此类而已。可是,又触痛我了。
我从不唾弃凡俗生活中的琐碎细节。我愿意和你一起领受,哪怕激情不再,哪怕面目蒙尘,哪怕彼此埋怨,哪怕平淡如水。只要能和你,从俗,或者超脱,又有什么区别呢?都是恩典。
只要和你在一起。
可是我们不能够啊。
你说你的生活被分成三个空间,有时能融合,有时生生撕裂。我想,恐怕我是不能成为你的全部了。虽然,你就是我的唯一。不是我真的甘心如此,而是我不能忍心去撕裂你。那么,就让我的痛苦和我的寂寞撕裂我吧。
我独自忍耐默默承受。
亲爱的克莱德,你要知道,我不是想责怪你什么。或者抱怨。毕竟,大多时刻,我都很快乐。或者,有时,我不是那么快乐,我只是坚持,不肯让痛苦掠夺了我的快乐。我不给痛苦涂脂抹粉,也不想顾影自怜,在自己的疼痛里面快慰,痛,是痛,血,是血,我不想假装一切不存在,就像我永远不能回避我们不能在一起一样。可是,痛,就痛吧,它不违背快乐。快乐也不违背它。它们是纯粹的,不扭曲。
它们组成了我们的爱。
我想,我要学会从点滴里体会你对我的爱。比如你昨夜写到三点半的、给小微的作业。比如你午夜临走前匆匆留言,告诉我我是你生命中的奇迹。比如清晨在公车上的短暂电话,想听我睡梦中的声音。我知道你心心念念挂住我。但愿你也知道我这样牵挂你。
有时,你微笑着而不对我说什么,我觉得这就是我已经等了很久的。
你。
我站在这里等你已久。
现在我在听《风继续吹》。那夜公车最后一排的位置上,你唱给我听,一句句翻译成普通话。只有那一句我抢先听明白了,是说:“我已令你快乐你也令我痴痴醉,你已在我心不必再问记着谁。”
痴迷醉。
你的邦妮
十二,九。凌晨
PS:以前念高中,每一年的“一二·九”都要演讲的。我喜欢参加这样的活动,最后一次,已经和他分手,就借着演讲告白,说,在历史书上有一页不敢随意翻过,因为太沉重太疼痛(下面一句我给忘了),有一个名字无法轻易说出口,因为一旦说出口,血会逆涌,泪会滴落。现在提起来,不太是怀念,反而是得意。在所有老师和全校学生面前,借着革命说爱情。你看我胆大包天。
·散文
永世不变的爱人
很多很多年之前,老师布置的作文,名为“我的爸爸”,我的第一句话是:在我们家里,爸爸和妈妈的差异,就像黑白照片一样鲜明。
如今,这么多年之后,重新拾起这个题目,我写的第一句话依然是这一句。
在我心里,爸爸和妈妈,像黑白照片一样鲜明。
我永远感激我的妈妈。我的自由天性都来自她。敏感,热烈,善良,纯朴,对生活充满希望,对爱情饱含憧憬,对美好事物的感恩,完整的牺牲精神,还有我一直在学习的,面对最不堪的打击的时刻,涌现出的巨大韧性。我的妈妈比我更像一个丰饶的大地女神。她一年四季永恒的短裙,一丝不苟地展现她修长的小腿,即便站着忙碌一整天,也不肯脱下七厘米的高跟鞋,清晨五时起身化妆,多年前那么封闭也敢敞开狭长的胸襟,露出雪白的乳沟,对着小学五年级的我教诲:“要的就是这味儿!”我的妈妈,高烧到神志不清,送她去医院前,她还要挣扎着爬起来说:“不给我化妆,我不出门!”
她对妆容的坚持,简直就是一种了不起的生活态度:一个女人,无论何时,都要美丽而骄傲地面对生活,高高地抬起自己的头颅。
可惜,这些,我完全没有继承下来。我活得太邋遢,太心不在焉。我的盛丽和妩媚,都只有爱才能开启:我就是《似水柔情》里的那个女人,白日里蓬头垢面,灰头土脸,在暗夜里迎接情人的时刻,穿上银白的缎子,黑发如流泉,馥郁神秘。没有得到我欢心的人,没有资格见识我的美和顺从。
我曾说,我对妈妈的爱和对爸爸的爱,是如此不同:如果我的妈妈,只是一个和我一丝血缘关系也没有的陌生女子,也毫不妨碍我欣赏她,爱她;可是,爸爸。
很长的时间,我都爱着我的父亲。
很长的时间,我都以为我不爱我的父亲。
我的父亲,在年轻的时候,是很英俊的。家里有老旧的黑白照片作证:那确实是一个好看的男人,轮廓深刻,浓眉大眼,端正而明亮,有一种坚忍纯全的气质。站在机床前,自信而满足,微笑着,全无磨砺和疲倦的痕迹。
其中有一张,是我从家里箱子底淘出来的,只有拇指那么大,镶嵌在小小的鸡心里,鼓鼓的。妈妈说,那是二十年前的玩意儿。可是我偷偷地挂在脖子上,一整个夏天。
妈妈喜欢说他们的情事。如何在大河里邂逅,如何一盘石磨定情,如何慌乱不能自持,如何面对流言飞语,如何毅然闪电结婚,如何白手起家。印象最深刻的,莫过于一日午后,她从楼上偶遇他,他瞟过来一眼,于是一日都不能安宁,后来得知,其实他根本没看见她,全只是自作多情罢了。说到这里,妈妈哈哈大笑。
而我,却总是在一遍一遍讲述中,恍惚就站在夏日的那个楼梯口,心脏激烈跳动好似要蹦出来。想看而不敢看,匆匆一低头走过。
小的时候,总是很骄傲有一个体面的父亲,穿白色长裤白色袜子,身形挺拔,心灵手巧,无所不能。那种近乎崇拜的孺慕。
而且,我一直都很害怕我的父亲。他很严肃,不苟言笑。不常发火,但不是宽厚,他时常忍耐郁结在心里,虚火上升,牙龈出血。喜怒不形于色,城府很深。三十岁生我,对我期望极高,因此十分严厉。在我印象中,我父亲从未称赞过我,即便是那些得奖的或者得意的文章,他也总是看不起,曾经一句“行文下流,像个文痞”的评价,使我伤心良久。妈妈的生气就像晴天下暴雨,来得快,去得也快,可是父亲不一样。他生气是结结实实的,又总是小病不断,记忆中,在饭桌上说话,老是要揣测他的脸色。
随着长大,妈妈的教训对我越来越不管用。家庭教育往往落在我爸爸身上。我最最害怕的就是他要给我上思想教育课,只要他说“我要和你谈一谈”,我就像面临离婚的夫妻一样,倦怠缩避,脸色发白。父亲口才不好,翻来覆去说的无非是那几句,就像坏掉的唱片,跳不过去。我简直记不清有多少个夜晚,父亲坐在我的小床上干巴巴地训导着我,讲一些要好好学习的大道理,叛逆少女眼巴巴地望着地面,心里想怎么还不快点结束。情景甚为奇特。现在,再也没有人教导我要怎么做,我的人生完全属于我,我突然有点怀念那种场面了。
我爸爸揍过我。是高二。一日,我的情书,塞在枕头底下的情书,被父母发现。晚自习结束,我回到家中,情书就摊在饭桌上。叠得小小的,从作业本上扯下来的纸,热烈而亲密的字句。他们一言不发地关上门,然后开始揍我。我的爸爸,抄起一把铁箍的雨伞,打击在我的背上,伞的布面破了,里面的铁骨被打断了,拉在我的脖子上,长长的一道血痕。他们叫我跪,跪了六个小时,要我认错,要我发誓再也不见他。血一涌一涌地冲在大腿上,麻木得没有知觉,我一滴眼泪也没有。我一点也不觉得我有错。我在捍卫我的爱情。我的冷漠激怒了父亲。他抓起我的头发,把我的头撞在了墙上。
这是那个从小不舍得动我一根手指头的爸爸啊,那个花了整个月工资给我买一件最洋气的滑雪衫,给我当马骑,给我做蒸汽小水车,一笔一画,在自己钉成的小黑板上,教我写“山海关”的父亲啊。
从那个时候起开始恨他。他不懂得爱情。他看《魂断蓝桥》说费雯丽活该。他不懂得艺术。他很世故。他很庸俗。尤其,他不懂得我。
记得那天是去拍护照的照片。一同去的是院子里和我同龄的一个女孩。我寒假在家,不修边幅到了极点,随意穿了件大毛衣就去了,披头散发。照相回来,爸爸激烈地数落我,说我太难看,太不会打扮,同去的女孩多么漂亮多么出众,把我说得一钱不值。我突然愤怒了。那是多么俗丽的漂亮啊,难道说,你的女儿竟然比不上这样的女人吗?如果说你的目标,是要把我培养成一个这样的女性,何苦要求我读那么好的书,何苦要浪费这么多年的时光?
我对着他,大吵一架,吵完大哭,委屈极了。
其实,后来,我才明白,我不能忍受的,不过是他,竟然用这个社会世俗的男人评判女人的眼光,来审视我。世上的男子都可以不欣赏我,蔑视我,冷落我,可是,你怎么可以?你是我的父亲啊!这世上如果只有一个男人可以毫无保留地爱我,欣赏我,难道不该是你吗?
又要到很后来很后来,我们拉锯着,撕扯着。他斤斤计较不厌其烦地叫我减肥,叫我穿高跟鞋,满屋子追着我叫我一定要穿内衣,比妈妈关心我的妆容百倍,我一步一步后退,妥协。最后,我终于发现,这个给予我生命的男人,残酷地给我上了第一课,使我认知,确乎世间男子便是如此庸俗而肤浅地看待女人,没有侥幸,没有例外。而我,只要一点点改变,就可以使他们觉得悦目顺眼。我终于可以使我的父亲满意了的时候,我也可以使大多数男人满意了。
可是,在我心底,我多么多么希望,他会对我说:“你是我最最美丽的小姑娘,小天使,无论怎么打扮,或者不打扮,你都是最可爱的!”我多么希望,他能这样来宠爱我啊!
在我十八岁之前,我和父亲没有交流。日常的对话,都只是事务对白。这在普通家庭中极其普遍。直到我考上了大学的那个夏天。我在高中的成绩烂透。出乎所有人意料,高考考了第一名。一整个夏天,家里都在大宴宾客,吃得我倒尽胃口。一个晚上,请的是我们四川的老乡,爸爸罕见地失控,喝醉了,烂醉。他对着我,喃喃地,毫不掩饰地说了又说,说了又说:“我们这些老乡的孩子里,就数你最有出息!”他像一个傻透了的老男人一样,口齿不清。
生平第一次,那种自豪席卷了我,我坐在那里,却觉得身体升腾得很高很高。我猛然觉得,其实这么多年以来,我是多么重视他对我的评价,我多么介意他对我的漠视,我是多么多么希望他能以我为荣,我突然觉得,其实我一直努力和叛逆,不过都是为了能得到他的肯定,得不到肯定,那么,只得到注意也可以。
他终于开始正视我了。小时候,我是那个被他抱高的小女孩,对视着他的眼睛,后来,我一直想跳高一点,让他看到我,可是他并不,现在,我终于长得足够高了。
我们开始对话。我们和解。我们心平气和有商有量。送我去念大学的最后一个晚上,在宾馆里,我和爸爸长谈到夜里三点。无所不谈,真正的成人那样的对话。此后,家里的大事小事都会征求我的意见。我的私事,也不再干涉。他甚至可以和我的小男朋友喝上一盅。
在我二十岁那年,我的书读不下去了。我在电话里,费力地向妈妈曲折表达这个意愿:我不想继续读下去了。我的妈妈,我一向以为最能理解我的妈妈,却带着她家庭妇女胆小和保守的本色,恐慌地拒绝我、安慰我,叫我忍耐到大学毕业再说。五一回家,这个念头不能淡,我打算寻个机会和父亲长谈一次,就像以前无数次他找我谈话一样。一个晚饭后,他却突然叫住我,非常轻描淡写地跟我说:“我想你的书还是不要念了,去北京吧。”
我的父亲,用他工人阶级朴素的智慧决定,不能继续吃亏,要另寻出路。他比我预料的远远要大胆得多。他说学位和学历都不算什么,学到东西才是真的。他的筹划和远见都使我目瞪口呆,我一言不发听从他的安排,我好似又重回那个伏在他膝下玩耍的小女孩,眼光带着崇拜。只要托付给他,什么都不用怕。
就在那个时候,我跟我自己说,我这一生最大的愿望,就是使他对我不失望。为了这个愿望,我什么都可以做。
也就是从那个时候起,我突然变得不叛逆了,变得无比之听话乖巧。我发现其实很多时候大人都是对的,一味反对无益,他们亦不是没有头脑,或许世界在变,他们显得落伍和弱小,可是,有时那老一套,确实是很管用的。我知道我这就是长大了。
长大以后开始喜欢成熟的男人。一次,捧着情人的面孔,突然发现这笑容和神态都如此相熟。我仔细审视着他每一个毛孔,是了,他多么像我的父亲。那种亲切,那种温暖,那种包容和宽厚。
我突然记起小时候妈妈不在,爸爸笨拙地给我梳头、洗头,那一双舒服的大手。考体育要锻炼,每日陪我长跑,回来给我按摩。第一笔大额稿费给他买了一件咔叽色衬衫,妈妈严厉指责我浪费钱,那衬衫料子不好,我委屈地哭,爸爸无言安慰我,抚摸我的头。奔忙在那间小小的饭店,扛着煤气罐,五十岁了他那脊背开始佝偻。
爸爸,爸爸。
我开始哭起来。
这世上我唯一可以毫无保留去爱的男人啊。
吴淡如的小说里,一个女人爱了一个男人三生三世都不得善终,最后一次转世,她决定做他的女儿。父亲,我想,我就是你亏欠了三生的冤孽。
而你,就是我永世不变的爱人。
……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