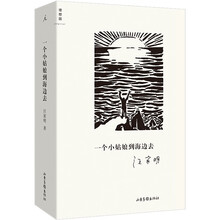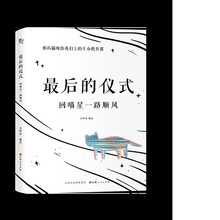他看着那人伸出了一只手。
“对啦!”马可勃暗暗的点着头,在一束禾苗的脚胫下拾起了一顶给浸得快要化掉了的帽子。
并且,这样的时间是一霎眼也不能迟缓的,他依照着那人的无声的吩咐,在那湿帽子的夹布里找出了一包类似炭灰一样的药物,丢进那人的嘴巴里。
过了一会儿,那人终于活跃地挣扎起来了。有一条很大的箫子蛇在他的手里给抓着,翻出了白色的肚皮,.一条长长的尾巴在半空里卷旋着。
经过了这件事,马可勃依着成年人的行径结识了那怪异的家伙,就是那个幸而让他救活了起来的捉蛇人。
不久,那捉蛇人却又让一条最毒的毒蛇咬死了。
马可勃,于是,重又退下来从成年人变成了小孩子。到一个村庄里去给人家牧马。
但是马可勃始终得不到一个安息的地方,主人没有留给他.一点儿的情面,因为他突然变成了冒冒失失的样子,在马尾上点着了火,把马尾烧掉了。
当他做了理发匠的时候,他还是觉得自己没有一点儿的成就,因为他鄙视着理发这一行业,他用自己积下来的钱买了好些把凿子和小刀,要去学习雕刻。
关于雕刻,他听过了一条故事。
这故事的好处:在于说这故事的人不在了,不晓得是从谁人的嘴里传下来的。他希望这故事能够在世上绝了迹,一那末,他将变成了这故事里的.人物,希望着这故事的再演。
马可勃于是游荡在他的神妙的幻觉中了。
但是,他天生着一付忠实的脸孔;他勤于做事,肯于受付托;从他的嘴里最容易得到答应。
马可勃在军法处受审问的时候,他变得越发驯良了,像是听从着理发店的师父师兄们杂乱的叫唤声,一下子扫地一下子拿刷子般的,那小小的脑袋忙碌地转动着;站在检察官的面前装着不曾听见或者不曾觉察的傻头傻脑的样子,于是是一件顶难的难事。
“这样的吗?——那样的吗?——”检察官的发问像剑子的锋梢般发亮着,尾随着他的口供,紧紧的追踪着。
“是的!”马可勃的心里,有着一条长长的退路,这退路恐怕是和那雕刻的故事,也有点儿关系的,“——炸弹,什么呀!——喳,是的,这炸弹——是那个挑夫契米多里,他从别处带给我的,我知道这件事。……”从那一百几十个囚徒的群中,契米多里,他被提到军法处来了。
听说这个人曾经拒捕,他的左手在和保卫队挣扎的时候给砍断了。他的妻曾经结识了一个牧师,在牧师那边知道了一种止痛药,那是所有的止痛药中最能止痛的一种,契米多里的创口一点儿也不要紧,有着这样的药在敷着。他原本就长得强壮而且高大,两条裤筒高高的卷在大腿上,一对巨粗的脚胫像弯弯的刀板一般,朝着相反的方向牢固地分站着。为着身上失了许多血,这下子他的神情变得有点儿憔悴了。
契米多里是梅冷城里的人,为梅冷和海隆两地间的商号输送货物的一个挑夫。
从海隆到梅冷,投有河流也没有铁道,只有一条峻险的山路,要流转彼此的货物,挑夫,这就是独一无二的交通利器。
契米多里参在从梅冷出发的挑夫群中,和平常时候一样,在正午以前到达了海隆。他们把货物分送给许多商号,再又从许多商号中接受了向梅冷方面输去的货物之后,依例是聚集在一间馆子里,解下了自己带来的干粮,没有带干粮的便吩咐店伙做几个黑面团。
契米多里有着别的任务。他连中饭也不在这里吃了。这一天,。一走进了海隆,便没有看到他的影子。
契米多里哪里去了呢?自己只管照料着自己的人们恐怕不会这样问。
这样,契米多里在一点儿也不受注意的时间里做完了许多事。
现在,他是可以回去的了。
但是,他必须把时间拖延下来。譬如往常回来的时间是在下午一点,那末这一次就必须拖延到两点,最好还是在两点以后,这样,在路上,他可以躲开了他的同伴们,避免许多无谓的阻梗,他们已经到了前面很远很远的地方去了。
一条小山溪,在那坚凝,峭厉的山谷里苦苦地挣扎着,幸而打通了一条小小的门径,冷冷朗朗,发出悠闲轻逸的笑声。从海隆到梅冷的山路,逶迤沿着那小山溪的岸畔走,小蛇儿似的,胆怯而又诡谲地,忽而,爬上了那挂着威吓的面孔的石堆,忽而,穿过那为长长的红脚草所掩没的小石桥。两边,高高的山峰,用着各种各样可惊的姿势,人对那小山溪所流过的地方俯瞰着,_而且无宁说是寻觅着。契米多里挑着沉重的担子,一步一步的喘着气,在一处有着野槐的浓荫的路旁歇息下来。他像一只吃人的野兽,在未曾把人攫在手里之前,却反而躲避起来了,简直有点儿怕见人。但是这当儿,路上走过了一个戴着第一号大草帽,有点儿像大商号的出海一样的人,接着是两个抬着空轿子的轿佚,……契米多里倾斜着上身站立着,吐了一嘴口沫,变换脚胫的姿势,这样的动作都似乎给予了可疑的材料,而他所干的事就要毫无隐匿的败露了!契米多里的经过是良好的,过了一会,他爬上一株高树去作一回嘹望,知道附近至少是半里之内再也没有一个过路人。契米多里于是把两条指头夹着拿进嘴里,用力的一吹,发出了哨子一样的尖锐的声音,接着,从那树林里爬出了一个人。这人是谁呢?契米多里不认识,但是他所认识的不是人的面孑L,却是一种共通的讯号。
契米多里终于说出了,——这是超过了一切的忍耐力的肉体的痛苦迫着他说的。他给倒吊在半空中,有三条夹着铅线绞成的皮鞭子在他的给脱得赤条条的身上连捷地交替着。
他晕了过去,又给用冷水喷醒来,另外,在那断臂膊的伤口敷着的药给扔掉了,换上了一包盐,在盐着。
契米多里怪声地叫着。
“……炸——炸弹——是从那——那人(从树林里出来的那人)的手里交给我的……”契米多里鼓着他那将近死去的活力说。
……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