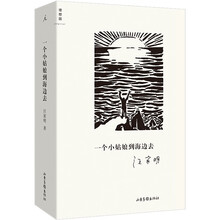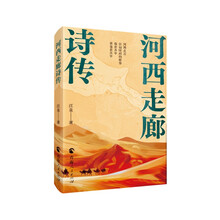这次是没想到,来京不一月便病了。不习于疾病的我,自然在平常从未有了解过这种滋味;朋友们也不常病,这样地少与疾病接触,以至我于这种滋味,更是漠然。
病大概是不重的,然而已经够难受了。躺着,静静的躺着,尤其是这一只头颅,是不能轻于移动的,卧着或起立,坐着或左右倾,都是破裂一般的疼痛。
要不是因循,自然不会渐渐地加重。终于抵抗不了这病魔的苦痛,于是在药房里买了一种药片,据说这是专治头疼而有极大的效验。服了,便立刻想趋除了这所感受的不堪的苦痛,但它竞不能如我所想的这般轻快。默默地忍受着罢,而又不甘于这样的苦闷,唯一的消磨一一也可以说藉以寻求安慰--便是一字一字地读着药片的发单,在浅显的单简的文句中,它夸耀它的灵验,那“药到病除”四字的力量,正与我所设想的与我所希求的完求一致,虽然事实并非如此。
负了苦痛的躯体在床上辗转着,月色布满了窗棂,夹竹桃枝叶交差的瘦影,迎了夜的秋风,在窗前微微地摇曳着,这种景象,极似江南修竹里的茅庵风味。以这样美妙的静夜,一瞬间曾作了清妙的默想:忘却了置身在这样烦乱的京城,几以为是深山的隐者。但是猛然觉着病,便不舒服起来,默想也因而变易了。这时曾默想到死,但并不新奇,不过是无聊的表现而已。
病人的心理,总是爱作死的默想罢。这是七年前的事了,那时我在汉口的一个中学里,偶然得了沉重的感冒,卧在三层楼上,这静寂的高楼,连同学的喧声都隔绝了。有时只能听着的仅是树杪的飘萧,与麻雀的嘈杂而已。我独自一人,除了叫苦的呻吟而外,便将镜子放在床里,对着镜子,扮出种种弥留时的死相。但是双眼并不紧紧地闭起,因为自己总还得要看一看这种死相的。热度渐高,神志昏眩的时候,便模糊地感到自己卧在竹床上,渡过了汉水的支流,奔驰在崎岖的界岭上,不懈地向故乡进发。病人之望医者,有如祈祷者之望圣灵,而卧病在异地的游子之望故乡,却与盼望医者并重。大抵是以为故乡的一山一水,都是却病的良药,至于温和的家庭,更不待说了。所以卧在鸾远的地方,孤零零地没有朋友,或所亲爱的,那悲哀的心怀,更易于蒙上乡愁的薄膜。
秋风劲厉,绿草亦尽萎黄,这正是荒凉大地的深秋。病人有如萎草,棉衣重重,犹不堪这深秋的凉意。曾一想到:独自出城,只骡漫游西出,在夕阳里,在骡背上,细玩着秋林红叶,也可以轻松了病中沉郁。但一觉着秋风恻恻地逼来,却又畏怯得如沙场逃归的战士。三日前,是旧俗的重阳节,回忆前年在故乡时,这一天犹着单衣,提着手杖,矫捷游山的兴致,已非今日病态龙钟可比。
偶然在院中看见房主人买了黄菊数株,因而想到故园的篱菊。重阳以后,便含苞吐放,那时不特叔父是终日忙碌菊事,就是疏放的我,也执着花锹,在菊根下轻轻地将土掘动,好从地下移到盆里。似这般极有清趣的劳力,就从未觉着疲乏。然而现在呢?人是在病着,天气却这样的凄清,虽然时节与往日未曾变易。
凉月的清晖,笼照着萧瑟的庭树,时一风吹,秋叶沙沙地响起;小病半愈,意绪更觉茫然,百无聊赖中,拉杂写此。
……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