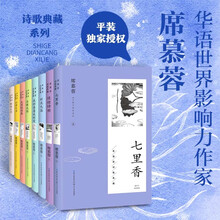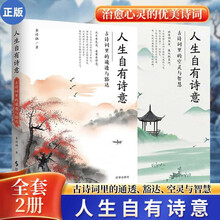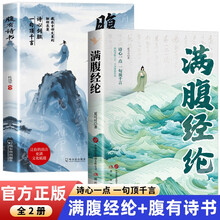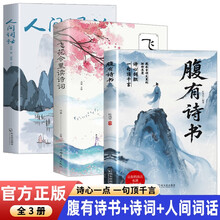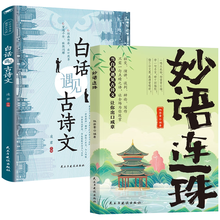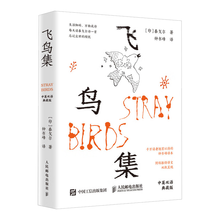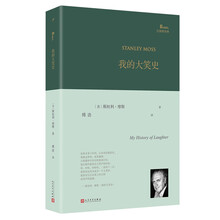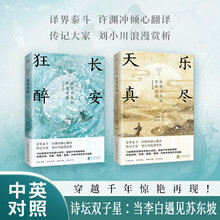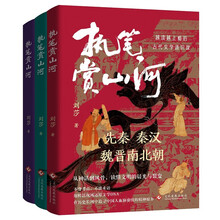这“十八高贤”中的宗炳(375—43),史称好游观,不舍远近,除庐山外,还西涉荆巫,南登衡岳,晚年回归江陵,仍余兴不减,将所历山川景物绘于居室壁上,叹日:“老疾俱至,名山恐难遍睹;唯当澄怀观道,卧以游之!”(《宋书·宗炳列传》)宗炳擅长书法、绘画和弹琴,尤其在山水画理论上卓有建树。他的《画山水序》,被认为是中国最早的研究山水美和山水画的学术专论。他在《画山水序》里指出山水“质有而趣灵”,“以形媚道而仁者乐”,道出了山水的外在美(质、形)与内在美(灵、道)和谐统一的旨趣所在,为以后文人由山水而悟道提供了一种审美依据。在这篇序文里,宗炳提出山水审美主张,即“含道应物”“澄怀味象”,认为审美者首先应具备“含道”(心中装有道)、“澄怀”(澄净胸怀)的素养或前提,方能体验山水之美、天地之美、宇宙之美。他还在该序里说明山水画家的职责乃是:“身所盘桓,目所绸缪。以形写形,以色貌色。”这句话的潜台词是:山水画家要用心来描绘山水,用心来聆听山水。宗炳把他所画的山水挂在卧室四壁,不仅继续游赏,还对着它们弹琴歌唱。宗炳观山赏水,听到了山水的合唱,进而领悟到自然的和谐之妙,领悟到“道”,从而才会笔有神助,画出有节奏美、和声美的顾盼生辉的山水画。这诚如清人布颜图《画学心法问答》所识:“宇宙之间,惟山川为大”;山水画家其实是“以素纸为大地,以炭朽为鸿钧,以主宰为造物。用心目经营之,谛视良久,则纸上生情,山川恍惚,即用炭朽钩定,转视则不可复得矣!此易之所谓寂然不动感而后通也。
”优秀的山水画家是用心去领悟山水,勾勒山水;优秀的山水诗人也是用心去触摸山水,歌吟山水。庐山的慧远和尚虽至死也未出庐山半步(大至以虎溪为界),却无数次地畅游庐山,足迹遍至庐山周围五百里内的山山水水。他的《庐山东林杂诗》与庐山诸道人《游石门诗》写庐山清气氤氲之美和山音泉韵之美以及“挥手抚云门”之趣、“驰步乘长岩”之唱,传递出莲社信众徜徉于大自然怀抱、且与大自然交感会通的心灵愉悦。他们的《游石门诗序》与《庐山记》(系慧远作品)则将庐山诸岭形势、山光水色描绘得形神备致,妩媚动人。《游石门诗序》还多次写到作者对山水的审美感受,如“触类之形,致可乐也”,“拥胜倚岩,详观其下,始知七岭之美,蕴奇于此”,“斯日也,众情奔悦,瞩览无厌”等等。这在审美体验上,比王羲之《兰亭集序》更加细致深入,可谓情景交融,而蕴藉隽永。论者以为该序“对后代的游记颇有影响。其由景立论,阐发佛理的方法,我们甚至可以在苏轼的《赤壁赋》中窥见它的影子。”东晋后期,佛教在经历了三百来年的韬晦时代后取得自立地位。慧远便是佛教自立的标志性人物。他开了佛教中国化之先河。他的《沙门不敬王者论》等五篇论文,为佛教的强势崛起挣足了面子。他在其山水诗文中顺便说佛,是很自然的事。值得注意的是,慧远之所以盛名远播,吸引来许多弟子,还因为他能谈玄,是继支遁以后东晋僧人中的又一位谈玄大师。他主张“内(佛)外(儒、玄)之道,可合而明”,说来说去是要争得佛学的主导地位。
随着佛学兴起,庄、老告退,在那些以浪迹天涯、纵游山水为旨趣的旅行者中,涌现出更多的僧人或优婆塞(男居士)。
《高僧传》卷六记载慧远的胞弟慧持,也是庐山东林寺高僧。他听说成都“地沃民丰”,又有峨眉秀峰耸峙,便借口“传化”而于隆安三年(399年)不顾兄长劝阻,决然离开庐山走上艰险的蜀道,十三年后卒于蜀中龙渊精舍。慧持人蜀沿途皆有山水之唱,据说也写得风韵标致,有其兄风范,可惜失传。李炳海先生说:“晋宋之际弥漫士林的浪游山水风气,虽然并不是源于庐山净土法门,但是,慧远师徒的所作所为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庐山净土法门的名僧高贤,实际上成了相当一部分山水名士的精神领袖”。
追随慧远上庐山的“十八高贤”中的刘遗民、周续之与当时居于庐山脚下的另一大隐陶渊明(352—427)并称“寻(浔)阳三隐”。刘遗民先为宜昌、柴桑二县令,后服膺慧远,去职上山,十五年后终老于此。周续之遁迹庐山,朝廷屡次征召不就,宋武帝刘裕谓之“真高士也!”他俩皆志在岩壑之闲远、水木之清华,为当时隐士中的佼佼者。
……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