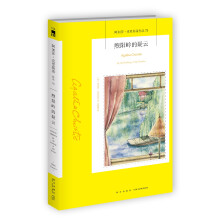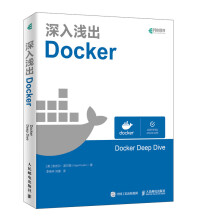第二节 逆水行舟,不进则退:从王士祯到沈德潜的“老调重弹”
明末清初提倡宋诗出现流弊虽然不足为怪,但有流弊,就会有人起来挽救流弊。这就为"返璞归真"势力的增强和活跃提供了新的契机。另一方面,宋诗本身不仅显示了一种独创精神,而且在总体上还体现了一种不同于唐诗的风格,尽管宋诗本身也包含了多种风格,宋诗的优秀代表都各有自己的面貌,但他们又有自己的共性。创作精神并不是审美对象,因此可以不受审美趣味的影响和制约;艺术风格却是审美对象,所以要受到审美趣味的影响和制约。不同的读者都各有不同的嗜好,不同的时期也各有不同的审美倾向。而诗人与读者一样也各有自己的审美爱好,同时在一定的时期也会体现出共同的审美追求。动乱时期与和平时期,不仅诗人对现实生活的感悟不同,而且审美追求也会有所区别。所谓“人情好尚,世有转移”(陆时雍《诗镜总论》)。而《礼记·乐记》则谓“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虽然诗歌艺术风格的性质并不完全由世运的盛衰所决定,但两者之间也有着曲折的联系,尤其是诗歌风格的情感因素确与世运的盛衰有着比较直接的关联。随着社会的安定,政局的巩固,诗歌表现的现实对象也就发生了改变。在紧张动荡的战乱生活煎熬中苟且度日的人们,也自然很向往和平、宁静、安详的生活环境,而现在这种愿望已经正在实现,人们自然会珍惜这来之不易的和平生活。康熙时期治国安邦的政治重心,也主要是“休养生息”,这是符合时代要求的。从政治角度来讲,统治者也需要一种"顺成和动"之音;对听惯了凄厉的哀泣之声的平民百姓来说,也希望能在"顺成和动"之音中享受宁静安详的愉悦,而和平生活本身也为"顺成和动"之音提供了客观条件。这上面的种种因素都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了清初以后的诗歌动向。朱彝尊曾自述诗歌创作的变化:“一变而为骚诵,再变而为关塞之音,三变而吴伧相杂,四变而为应制之体,五变而成放歌,六变而作渔师田父之语。”(《荇溪诗集序》)姚鼐评査慎行诗亦谓:“国朝诗人少时奔走四方,发言悲壮;晚遭恩遇,叙述温雅,其体不同者莫如查他山”(《方恪敏公诗后集序》)都说明了个人生活经历的变化,对诗歌创作的影响。而郭曾沂比较“江左三家”、“岭南三家”与“国朝六家”诗歌的区别也指出:“六家诗继三家起,盛世元音便不同。”(《杂题国朝诸名家诗集后》)也注意到了战乱时期的诗歌与和平时期的诗歌各不相同。而在康熙时期影响最大,较能体现和平之声的诗人是王士祯。清初以后诗歌主要趋向发生改变与他的神韵说很有关系。
王士祯早年学诗爱好明代徐祯卿、高子业之诗,徐高之诗属于“古淡清音”一派。王氏家法虽传两李诗学,但王士祯心香一瓣却并不在杜甫,而在王、孟一路,故王士祯虽然学唐,但与两李取径不同。张九徵曾赞王士祯说:“夫历下诸公,分代立疆,矜格矜调,皆后天事也。明公御风以行,飞腾缥缈。……然则明公之独绝者先天也,弟知其然,而不能言其然,杜陵云:‘自是君身有仙骨,世人那得知其故’,此十四字足以序大集矣。”(周亮工《赖古堂尺牍新钞》录张九徵《与王阮亭》)当时人已经看出王士祯之才性与李攀龙他们不同。顺治十四年秋,二十四岁的王士祯游历下,赋《秋柳》四章,显示了与明七子呆板、滞重完全不同。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