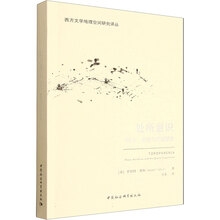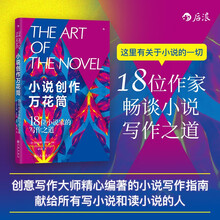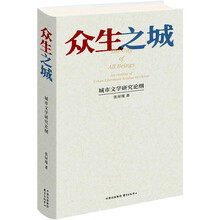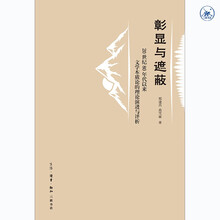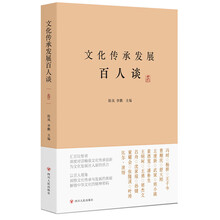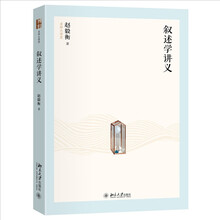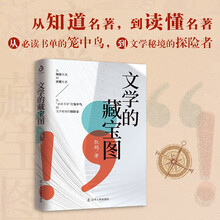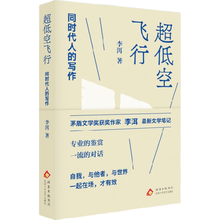或许由于这种隔绝和短暂的历史,其结果是,对民族叙事和历史中对政治功能的质询在澳大利亚相对较晚才出现。历史和文学学科二者在获取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理论的益处上均显得反应迟钝。其结果是,尽管历史和文学研究对于“民族性”产品感兴趣,但却没有可能使其继续研究下去的理论工具。然而,从80年代开始,随着人们对后结构主义和叙事学更为了解,文学学者(以及后来历史学家们)开始接受这样一种观念,即民族性或许是文化虚构、叙事以及巴特概念上的神话的相当不确定的产物。这一次出现了在理论上的首次尝试,将澳大利亚文学视为一种文化产品提供了解释方式(Hodge and Mishra;Schaffer;Turner,《民族小说:文学、电影和澳大利亚叙事的构建》;White),其中在澳大利亚文学研究、澳大利亚历史研究和澳大利亚文化研究之间有一种清晰可见的跨学科的促进方式。
在这一时期英国文化研究倾向于“避免命名(exnominate)”民族性领域,追随这一潮流的澳大利亚人却明确无误地关注民族文化所附加的意义,关注通过这些意义所强加的包容和排斥的模式及其为之服务的利益。倘若80年代英国文化研究将“民族文化”视为某种完全吸引了保守派文化政治的东西,因而并不值得为之费心的话,澳大利亚文化研究则将其视为完全值得论争的东西。所以,许多早期的澳大利亚文化研究集中研究“澳大利亚”在所有文本和媒体中是如何被表征的,以及这些表征的后果及影响。这类研究的焦点包括在多元文化主义之下对本土澳大利亚人以及非盎格鲁一撒克逊族裔的表征。澳大利亚文化研究逐渐地融入国际论坛有助于在90年代后期扩展这些论争,使其成了一个并不那么带有民族主义倾向且在政治上更加多样的探索领域。
英国对澳大利亚文化研究的影响尽管仅仅只是众多汇入的分支,然而的确是有意义的。英国伯明翰大学当代文化研究中心对意识形态的理论化,以及稍后对葛兰西霸权的解说曾经影响巨大,而且在某种程度上依然保持着影响。首先,斯图亚特·霍尔以索绪尔和巴特符号学的方式对文本解码与编码的论述,是一种根本性的分析工具(Fiske,Hodge,and Turner)。然而其他并非源自伯明翰的传统也具有影响或穿透力。例如,本土电影和媒体分析传统就是70年代与政府资助的澳大利亚电影工业复兴并行发展起来的。该传统在开始时也是由民族主义所支配,或至少是由反帝国主义政治及为本土受众保护本土电影产品的宗旨所支配。开始时,方法论的倾向是政治经济,然而这一点后来最终让位于民族文化与电影、电影文本的文化政治与电影之间的联系(参见O'Regan)。在80年代并行的发展中,这一发展与文学和文化理论的论述推进相关,有一种理论论述上的成熟,这些论述受到梅斯符号学和拉康对西格蒙德·弗洛伊德理论挪用的影响(参见雅克·拉康、关于克里斯蒂安·梅斯的相关内容,请参见电影理论与批评)。
……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