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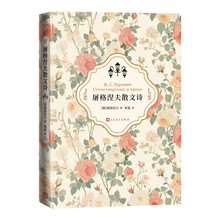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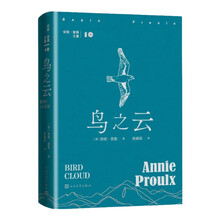


第1场
伽里玛先生的牢房。巴黎。现在。
灯光渐强,显露出在一问牢房内的65岁的瑞内.伽里玛。他穿着一件舒适的浴袍,显得衰老而疲惫。摆设简单的牢房内,有一只木质的板条箱,上面放了一个轻便电炉和一只水壶,还有一台手提磁带录音机。伽里玛坐在板条箱上盯着录音机,一丝忧郁的微笑从他脸上浮现了出来。
舞台后部,穿着传统中国服装的宋丽玲,以一个漂亮女人的面目出现了,在中国音乐的铿锵的敲击声中,她舞蹈着,表演着京剧中的一个传统段落。
接着,渐渐地,灯光和声音同时淡出;京剧的音乐融入一幕西方的歌剧、普契尼的《蝴蝶夫人》的“爱的二重奏”的乐声中。在西方特色的音乐伴奏下,宋丽玲继续舞蹈着。尽管她的动作是相同的,但现在,不同的音乐使它们具有了芭蕾的特质。
伽里玛站起来,转向舞台后部,看着宋丽玲的身影,宋丽玲对伽里玛视若不见,继续舞蹈着。
伽里玛:蝴蝶,蝴蝶……
(当宋的身影淡出后,他强迫自己转过脸,开始对我们讲话。)
我的牢房就这么大:四米半宽,五米长。正对着的高墙上有一个窗户,还有一扇门,非常结实,它让我远离那些喜欢让人签名题字的人。我就对这台磁带录音机、这个轻便电炉,还有这张可爱的咖啡桌负责。
当我想吃东西的时候,我就被带到餐厅去——发烫的、热气腾腾的汤汤水水就会出现在我的盘子里。当我想睡觉的时候,电灯泡自己会关掉——这都是仙女们干的。我待的这个地方让人心醉神迷。法国人——也就是我们,知道怎么管理一个监狱。
可是,老实说,我没被当成一个普通囚犯来对待。为什么?因为我是个名人。你瞧,我把大家给逗笑了。
我从来没有梦想到这一天会到来。我也从来不是个聪明幽默或者机灵的人。实际上,当我还是个小男孩的时候,在我的文法学校的同学中所做的一次非正式的调查中,我被一致认为是个“最不可能被邀请去参加聚会的人”。这是一个我多年来设法保持的头衔。尽管也有一些强烈的竞争。
但现在,变化多大啊!看看我:巴黎的每个正式的社交集会的灵魂人物。巴黎?为什么要谦虚呢?我的名声已经传到了阿姆斯特丹、伦敦、纽约。听听那些人说什么吧!这都是世界上最时髦的会客厅。我就是那个让他们精神振奋的人。
(伽里玛用一个夸张的手势把我们的注意力指向舞台的另一个部分。)
……
——《时代》周刊
“《蝴蝶君》有时会被认为是一部反美国的戏剧,是对西方支配东方,男人支配女人的模式化观念的一种谴责和反对。恰恰相反,我把它看成是对各方的一个请求,希望它能穿透我们各自的层层累积的文化的和性的误识,为了我们相互的利益,从我们作为人的共同的和平等的立场出发,来相互真诚地面对对方。”
——黄哲伦
“希望这个剧本能够帮助更多的中国人认识到我们是谁,同时也认识到把我们变成我们的‘他们’是谁。”
——张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