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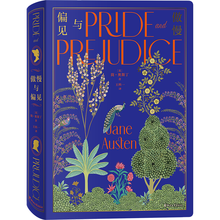


第一章 一位善良的人
二月,一个天气凛冽的傍晚,有两位绅士正坐在肯塔基州P城一间摆设考究的客厅里把酒换盏。他们身边没有仆人,彼此椅子也靠得很近,仿佛在一本正经地商量什么事情。
为了行文方便,我们到现在为止只说是两位“绅士”。不过,倘若挑剔地打量一番,其中的一位,严格说来或许还够不上绅士身份。这人矮小粗壮,五官猥琐,其貌不扬;那矫饰狂妄的做派,说明他是一个蝇营狗苟,一心想跻身于上流社会的小人。他衣饰过分讲究:俗气的花马甲,缀着黄点的刺眼蓝围巾,外加一条向人炫示夸耀的领带,刚好跟他整个派头相吻合。他粗糙肥胖的手上戴了好几枚戒指;身上佩一条沉甸甸的金表链,上面系着一串光怪陆离的惊人大图章。谈得兴浓的时候,习惯地把表链摇晃得叮当作响,流露出一副志得意满的神情。言谈话语之中,随心所欲、信口雌黄地违反莫里氏语法规则,还时不时夹带着各种亵渎神明的言词。这些言词,即使是希望我们叙述得活灵活现的想法,也不可能让我们把它们笔录下来。
他的谈话对手谢尔比先生,却有一副绅士仪表;从他住宅的布置,以及家务管理的总的情况来看,都表明他的家道小康,甚至于殷实富裕。如前所述,这两个人正在一本正经地交谈着。
“叫我看,事情就这么办吧。”谢尔比先生说。
“我可不能这样做生意,绝对不能,谢尔比先生。”另一个说,一边端起葡萄酒杯对着灯光端详着。
“说实话,黑利,汤姆不比寻常;无论怎么说,肯定都抵得上这笔钱。他踏实可靠,又有本事,我整个庄园他都管理得有条不紊。”
“你是说像黑鬼子那样可靠吧。”黑利说着喝了一杯白兰地。
“不是这个意思,我是实话实说。汤姆是个踏实虔诚、明白事理的好奴隶。他四年前在一次野营布道会上信了教,我相信他不是假装的。从那以后,我就把所有家产托付给他,钱财也好,房子也好,马匹也好,统统交给他管,允许他在这一带地方出出进进。无论什么事,我发现他总是忠心耿耿、老实厚道。”
“有些人不相信会有虔诚的黑鬼子,谢尔比,”黑利说,一面坦率地挥了挥手,“可我相信。我上次贩到新奥尔良去的那批黑奴当中,就有这样一个家伙。听他的祈祷真跟在教友聚会上一样。那家伙不声不吭的,挺听话的样子,还给我卖了个好价钱。有个人不得不把他卖掉,我就捡了个便宜,把他出手时我赚了六百块钱。是啊,我看要是货真价实的货色,黑鬼子信教倒是好事。”
“唉,汤姆可是个货真价实的货色,再没有什么奴隶能跟他相比了,”谢尔比答道,“就说去年秋天吧,我让他一个人到辛辛那提给我做生意,回家时带回了五百块钱。‘汤姆,我信赖你,’我对他说,‘因为你是基督教徒,你决不骗人。’汤姆自然回来了,我也知道他会回来。听说,有些不三不四的家伙曾经对他说:‘汤姆,你干吗不往加拿大跑?’‘哦,老爷相信我,我不忍心。’这事是别人告诉我的。跟汤姆分手,我心里很难过,真的。你应该让他抵偿债务的全部差额,黑利。要是你还有什么良心,你会这么办的。”
“我告你说,买卖人能够有多少良心,我就有多少良心。而且,你也清楚,也许只有用来发誓赌咒的那么一点点,”奴贩调侃地打趣,“不过,论起朋友来,只要合情合理,我什么事都愿意干。可是这件事,你瞧,有点太叫人为难,太叫人为难啦。”奴贩若有所思地叹了口气,又倒了些白兰地。
“那么,黑利,你想怎样成交这笔生意?”谢尔比尴尬地沉默了一会儿说。
“难道除了汤姆,你就不能再匀上一个小子或者丫头?”
“得得,我一个也匀不出来。实话实说,要不是处境艰难,我决不愿意出卖奴隶,不想失去人手,这是实情。”
这时门开了,一个二代混血小男孩,大约四五岁的样子,走进餐厅。小男孩长得分外清秀,招人喜爱。一头黑发,像毛茸茸的丝一般纤细发亮,打着卷儿,贴在长着酒窝的圆脸蛋上;那双又黑又大的眼睛,柔和而炯炯有神,从浓浓的长睫毛下,向厅里好奇地张望着。一袭红黄格子花呢的鲜艳罩衣,精心缝制得十分可身,更加烘托出孩子黧黑的漂亮风采;一副颇为自信的滑稽神情,夹杂着忸怩羞怯,说明孩子对主人的宠爱和眷顾已经习惯。
“嗨,吉姆·克娄!”谢尔比先生说着吹了一声口哨,丢给他一把葡萄干,“捡起来吧!”
孩子使尽力气,一蹦三眺地朝奖赏奔去,主人这时也朗朗大笑起来。
“过来,吉姆·克娄!”主人说道。孩子走过来,主人拍拍他那鬈毛脑袋,又抚摸了他的下巴一下。
“来,吉姆,给这位先生显显本事,唱唱歌、跳跳舞。”于是,孩子唱起了一支在黑人当中流行的粗犷而又怪异的歌曲,声音清晰洪亮,随着歌声,手脚和整个身子也做出了许多滑稽可笑的动作,但都同音乐旋律完全合拍。
“太棒了!”黑利说,同时把半个橘子扔给他。
“来,吉姆,学学得风湿病的卡德乔大伯走路。”主人说。
转眼之间,孩子灵活的手脚似乎残废得变了形。他驼起脊背,手里拄着主人的手杖,蹒蹒跚跚在屋里走着,孩子气的脸上满布皱纹,一副发愁的神色,并且学着老人的样子,左一口右一口地吐痰。
两位绅士都哈哈大笑起来。
“来,吉姆,”主人又说,“让我们看看老罗宾斯是怎样领唱赞美诗来着。”孩子把丰满的脸庞拉得老长老长,煞有介事地开始用鼻子哼出一首赞美诗的曲调。
“好!太棒了!多棒的小后生!”黑利说,“我承认,这后生是个好货色。告你说,”他说着说着用手猛地拍了下谢尔比先生的肩膀,“搭上这后生,我就了结这桩买卖——一定了结。得了吧,这可再公道不过啦。”
就在这当儿,门轻轻地推开了,一个二代混血的年轻女人,年纪约在二十五岁上下,走进屋里。
只需从孩子到女人打量一眼,就能断定她是孩子的母亲。那丰润的黑色圆眼睛,配着长长的睫毛,那丝一般的黑色鬈发,都同孩子的一模一样。棕黄的肤色在她的脸颊上消退了,泛起了一片可以觉察得到的红晕。当她看到那个陌生男人在直勾勾地望着她,狗胆包天地露出毫不掩饰的遐想时,红晕变成了一片绯红。她的衣裙极为整洁合身,益发衬托出她身材的窈窕丽质。纵使是她纤细姣美的酥手,以及她腴瘦合度的玉足和脚踝等外部的细枝末节,也逃脱不了那个奴贩机敏猴精的眼睛。他可谓深通此道,抬眼望去,就能把一个姣美女奴的方方面面一览无余,尽收眼底。
“什么事,伊丽莎?”主人问道。她停下脚步,犹豫不决地望着主人。
“对不起,老爷,我找哈利。”孩子一个箭步,窜到她跟前,拿出罩衣边沿里兜着的战利品让她看。
“好,那么把他带走吧,”谢尔比先生说。她于是怀里抱着孩子,急急忙忙退出屋去。
“老天哪!”奴贩馋涎欲滴,转身冲着谢尔比说,“真是件好货色!这丫头要在新奥尔良,你随时都可以发一笔财。我平生见过的一手交钱一手交货的丫头,少说也得干把个,可没有一个比这个漂亮。”
“我可不想拿她来发财,”谢尔比先生口气冷淡。他想转变话题,便打开一瓶新鲜葡萄酒,问黑利好喝不好喝。
“棒极了,先生,头等货!”奴贩说,然后转过身来,亲昵地拍了拍谢尔比的肩膀,补充道,“唉,这丫头你打算怎么卖?我出什么价?”你要什么价?
“黑利先生,她不出卖,”谢尔比先生说,“你就是拿出等身的黄金,我太太也不愿跟她分手。”
“啧、啧、啧!娘儿们家总是这样唠叨,她们压根儿算不过账来。要是叫她们知道,等身的金子能买多少手表、衣服、首饰,我看,情况就不一样啦。”
“我跟你说,黑利,这件事从此不要再提;我说不卖就不卖。”谢尔比毫不动摇。
“那么,你总得给我饶上那个小后生吧,”奴贩说,“你一定看得出来,我对他可够大方的了。”
“你要个孩子顶什么用?”谢尔比说。
“我有个朋友打算做这行当生意——想买进漂亮的小后生,养大了到市场上去卖。这可是地地道道的高档货——卖给买得起漂亮后生的有钱人,当个听差什么的。那些大户人家有个真正漂亮的后生开门、听差,照应照应,有多体面。他们能卖一大笔钱,这个会唱歌的小鬼头,是个多么滑稽的小东西,正是件好货色。”
“我可不愿卖掉他,”谢尔比先生若有所思,“说实话,先生,我生性慈善,不愿意把孩子从他妈妈手里夺走,先生。”
“哦,你不愿意——老天,是啊——是这么档子事儿。这我全懂。有时候,跟娘儿们打交道,叫人心里窝火,又吵又嚷的,我啥时候都受不了。她们特别让人不舒心;可我干起买卖来,总是躲开她们,先生。噢,你把那女人支开一天或一个礼拜左右怎么样;那时候,事情就神不知鬼不觉地办利索啦——她回来时,一切都过去啦。你太太可以给她买副耳环,买件新的长外衣,或者买些小首饰,算作补偿。”
“我看不行。”
“上帝保佑你,是不行!这些黑鬼不像白人,这你清楚。事情办得不对头,他们多会儿也忘不掉。人们说,”黑利说着装出一副坦然直率而又推心置腹的样子,“这种买卖会让人心肠变硬,可我压根儿不这样看。说实在的,我从来不按有些人干买卖的样子办。我见他们从女人怀里夺走孩子,把孩子卖掉,女人却一个劲儿地又喊又叫,简直像疯了似的。这办法不好。这会把货物弄坏,有时还会叫孩子们没法听差。有一次,在新奥尔良,我就见过一个顶顶漂亮的丫头就这么给毁了。买她的那家伙不想买她的孩子;可她生起气来,简直让你难以招架。告你说,那女人怀里紧抱着孩子,嘟嘟囔囔,真叫人害怕。一想起这件事,我心里就有点发怵。他们抢走了孩子,把她关起来,她还疯疯癫癫,唠叨个没完,不出一个礼拜就死啦。一千块钱算白搭了,先生,只是由于缺少手段——情况就是这样。发发慈悲总是上帝,先生;这是我自个儿的经验。”说着,奴贩向后靠在椅子上,叉起两只胳膊,露出一副决心积德的神情,俨然自诩为威尔伯福斯第二。
看来,这个话题引起了黑利的浓厚兴趣;在谢尔比先生若有所思剥着橘子的时候,他仿佛迫于真理力量的使然,却又带着恰到好处的踌躇说了起来。
“一个人夸奖自个儿,看起来不太合适,不过,我这样说又恰恰是实情。我看,在人们买进的黑鬼当中,我买的那一群群黑鬼,算是顶呱呱的——起码人们是这么对我说的。要说我曾经干得漂漂亮亮的,那么屈指算来,这种情况就有上百次——个个情况都很好——膘肥、刮净,赔本的事跟干这一行的买卖人一样,很少很少。我这把它算在我善用手段的账上,先生。我告你说,先生,慈悲是我经营手段的顶梁柱。”
谢尔比先生一时语塞,只是说:“居然如此!”
“这会儿,人们笑话我的想法,先生,人们责备过我,先生。这些想法不时兴,也不寻常,可是我信守这些想法,先生,我按这些想法去办。这些想法让我发了大财,是这样,先生。我可以说,这些想法叫我一路顺风。”奴贩听到为自己的打趣大笑起来。
对慈悲的这些解释里,透着泼辣辣的新意,谢尔比先生不禁同黑利一起放声大笑。亲爱的看官,你也许会笑出声来。然而在现今世道上,慈悲以形形色色的奇怪形式表现出来,而慈悲人士的所言所行,就更罄竹难书。
谢尔比先生的笑声为奴贩接着说下去增添了勇气。
“嗨,说来也怪,人们的脑袋里,根本听不进这个去。喏,在纳切兹,我有个老搭档汤姆·娄克。他可是个精明的家伙。这没错儿,只是对待黑鬼活像个魔鬼——从原则上说是这样,明白吗?因为,好心肠的人从来不砸别人的饭碗。这是他的处事方式,先生。以前我都不断劝汤姆。‘哎,汤姆。’我时常说,‘你的黑丫头片子要是动了气,哭叫起来,打她们的脑袋,给她们皮棰,又有什么用呢?这太荒唐啦!’我说,‘什么好处也没有。哎呀,就是她们哭叫,我看也没什么坏处,’我说,‘哭是天性,’我说,‘而且,天性不从这里发泄,就会从其他地方发泄出来。再者说啦,汤姆,’我说,‘你这么干会毁了你的丫头,她们会生病闹灾、垂头丧气,有时还会变得丑陋难看——特别是那些胆小的丫头。这都是你那魔鬼脾气跟拳打脚踢弄的。得啦,’我说,‘你干吗不哄着她们点,夸夸她们呢?听我的话,汤姆,捎带着发点慈悲比起打骂来管用多了。这样做好处更多,’我说,‘别不信我说的话。’可是,汤姆硬是学不会这种诀窍;给我毁了好些丫头。所以,我不得不跟他散伙,虽说他心肠不错,是个干买卖的好手。”
“那么,你是不是觉得你生意经营得比汤姆好?”
“啧,当然啦,先生,可以这样说。你瞧,但只做得到,我总是略微注意一下出手小孩子等这类不愉快的事情——把丫头们带走——这叫眼不见心不乱。等事情办利落,又有补救办法时,她们自然就习惯了。你明白,这可跟白人不一样。白人长大成人后,人们希望他们赡养妻子儿女什么的。可规规矩矩抚养大的黑鬼子呢,你也清楚,什么希望都没有。所以说,这类事情办起来并不费事。”
“那么,恐怕我的黑奴不是规规矩矩扶养成人的。”谢尔比先生说。
“我看也不是,你们肯塔基州的人把黑鬼惯坏了。你们用意是为他们好,可到头来,这并不是真正的仁慈。你明白,一个注定在世上挨打流浪的黑鬼,要是卖给汤姆,或者迪克,或者不论是谁的话,教给他那些想法和希望,根本不是什么仁慈,因为,后来的煎熬跟流浪,他更受不了。我大胆说一句,要是换个地方,你那些黑鬼子肯定会耷拉下脑袋的。可你种植园里的黑鬼子反而会拼命似的又唱又叫。你明白,谢尔比先生,自然人人都觉得自己的办法好,我也觉得自己是按照黑鬼子的身价来对待他们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