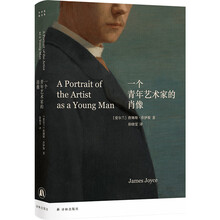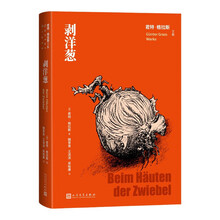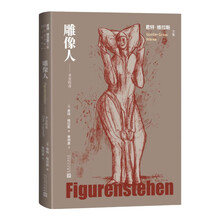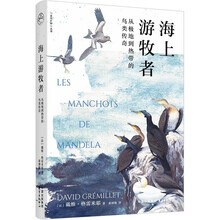顺便提一下,我的朋友,作为艺术品,作为历史的表现形式,它的价值还是稍高于那冰冷、灰白的建筑物。因为这个建筑物显得杂乱无章,它的三个正面堆砌着拱门饰,它的装饰廉价、俗气、单调,一切都只是简单的重复,没有任何闪光点,它的屋顶也不完整,既没有屋脊,又没有烟囱,今天,某些泥瓦匠正用这样的方式,甚至在我们美丽的巴黎城面上,淹没着博卡尔多的迷人杰作。我们真是奇怪的人类,我们任凭特莫伊市政厅被摧毁,却又建起了这种东西!看到那些自以为是、自称是建筑师的人偷偷地将建筑物降低了两三法尺,也就是说他们完全改变了多米尼克·博卡尔多的可爱的尖屋顶,以便能够同他们发明的难看的平屋顶相配套,我们的心里真是难受极了!我们难道将永远是这样的民族吗——欣赏高乃依,却又让安德里厄先生来修改、删除、改变高乃依的风格!——好吧,还是回到科隆的话题来。
我登上了警钟楼。天色阴沉,这和建筑物以及我的心情倒是非常协调,从这里,我看到整座可爱的城市就在我的脚下。
科隆位于莱茵河之上,就如同鲁昂位于塞纳河上,安特卫普位于埃斯考河上,就像所有依傍在一条天堑般的大河旁的城市那样,它的形状就像是一个绷紧了的弓,河流就是那弓弦。
房顶上的石板瓦层层叠叠,顶部尖尖的,就像是折成两下的纸牌,街道狭窄,有着结实对称的人字墙。在房顶上面到处可见一条城墙和砖石城壕的暗红色曲线,紧压着城市,如同一条系住河流的皮带,下游是图尔姆森塔楼,上游是漂亮的拜恩杜姆塔楼,在其雉堞上,耸立着一尊大理石神父像,正在为莱茵河祈福。从图尔姆森到拜恩杜姆的莱茵河沿岸延伸着一法里长的窗户和建筑。在这长长的线条中间,有一座大浮桥,优雅地拱曲在水流之上,这座桥穿过宽宽的河流,直达对岸,将多伊茨这座白色房屋的小城和科隆的黑色大建筑群连成一片。
在科隆高地上,在片片屋顶以及长满鲜花的座座塔楼和复折屋顶中间,矗立着二十七座教堂的各式塔顶,不算科隆大教堂,这其中还有四座庄严的罗曼风格的教堂,它们形式各异,却一个个宏伟瑰丽,不愧为真正的大教堂。北边是圣马丁大教堂,西边是圣热雷昂大教堂,南边是圣阿波特尔大教堂,东边是圣玛丽·卡皮托里大教堂,它们呈圆形矗立着,就好像是半圆形的后殿、塔楼和钟楼合在一起的巨大的纽结。
如果我们仔细观察城市,真是热闹非凡,生机勃勃;桥上挤满了行人和车辆,河流上帆船密布,沙滩上尽是桅杆。所有的街道都是密密麻麻的人群,所有的路口都在交谈,所有的屋顶都在歌唱。不管是这儿,还是那儿,绿色的树丛温柔地抚摸着黑色的房屋,在单调的石板瓦屋顶和砖石建筑群中,时而可以看到十五世纪老式旅馆那雕刻着花朵、水果或树叶的长长的屋檐,鸽子欢快地飞来栖息在上面。
这个大城镇,工业使它成为商业闹市,地理位置使它成为军事重地,河流使它成为水边城市,在它的周围,朝着各个方向,平铺延伸着一片广袤富饶的平原,因下沉一直延至荷兰的一边,莱茵河时不时地从中穿过,在东北方向围绕着历史上著名的七座小圆丘,它们由于传统和传说成为奇妙的圣地,人们把它们称为七山脉。
就这样,荷兰及其商业,德国及其诗歌,作为人类思想的两个面貌:实利和理想,两者矗立在科隆的地平线上,而科隆本身就是一座交易与梦想的城市。
从警钟楼下来,我止步于院子里那文艺复兴时期迷人的门廊前。我刚才把它叫做“凯旋门廊”,其实,我本应该说是“辉煌门廊”,因为这个精美建筑物的第二层是由~系列的小凯旋门组成的拱廊,上面按照年代附着题词:第一个是献给恺撒的,第二个是献给奥古斯特的,第三个是献给科隆的创始人——阿格尔巴④,第四个是献给基督教皇君士坦丁的,第五个是献给立法皇帝朱斯第尼安的,第六个是献给在世的皇帝马克西米利安。在门廊的正面,富有诗意的雕刻家雕出了三幅浮雕,代表着三个驯狮师:米隆·德克多,矮子丕平和达尼埃尔。在两边,是米隆·德克多用身体的力量将狮子掀翻在地,以及达尼埃尔用精神的力量征服了狮子。在达尼埃尔和米隆之间,作为把两人互相连接在一起的自然连线,上面安置的是矮子丕平,他混合了士兵强健的身体力量和精神力量来对付这些凶残的野兽。在纯力量和纯精神之间,勇气胜出。在竞技者和先知之间,英雄胜出。
丕平手持宝剑,左手裹着大衣,伸进狮子的嘴中;狮子张牙舞爪,后脚直立,这种奇妙的姿势在徽章中叫做“雄狮挺立”。丕平英勇地面对着它,与它战斗。达尼埃尔一动不动地站立着,双臂下垂,两眼仰望天空,而狮子正充满爱意地蜷缩在他的脚下,精神不战而胜。至于米隆·德克多,他的双臂困在树上,他奋力挣扎,而狮子却将其吞噬;这是盲目而愚蠢的驯狮法的灭亡,他们曾相信他们的肌肉和拳头能对付一切,然而纯力量被打败了。这三幅浮雕都具有深刻的意义。最后一个则是可怕的结果。我不知道从这忧郁的诗歌中能得出什么样的可怕而宿命的结论,也许雕刻者本人也不知道。这是大自然对人类的报复,植物和动物有着共同的利益,里面的橡树就是来给狮子帮忙的。
不幸的是,拱门饰、浮雕、柱顶盘、拱墩、柱顶盘上楣以及柱子,整个漂亮的拱门廊都被修复了,刮去原来的,重新嵌了灰缝,刷了油漆。整个过程干净利落,干净利落得让人伤心。
正当我要从市政厅出来的时候,一个男人走进了院子,与其说他年岁大,不如说是苍老;如其说他的背有点驼,不如说有失庄重,外表看起来穷困潦倒,举止中却又透出几分傲气。带我上警钟楼的门房示意我注意他。这个男人是位诗人,他依靠年金在陋室里写一些史诗。他的名字倒是绝对的默默无闻。我的向导对他极其崇拜,他对我说,这个男人写了一些史诗反对拿破仑,反对1830年革命,反对浪漫主义,反对法国人,他还有一首美丽的史诗是呼吁科隆现在的建筑师们按照巴黎先贤祠的样子,继续大教堂的修建。暂且接受他写的就是史诗吧。但这个人却是少有的邋遢。在我的一生中还从来没有见过一个这么不修边幅的怪人。我觉得在法国,我们找不到能与之相比较的史诗诗人。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