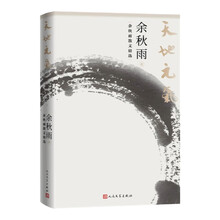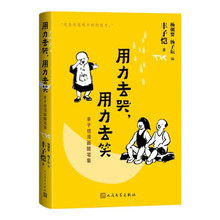不懂希腊文化
自称懂得希腊文化是虚荣而愚蠢的,我们的无知大概相当于任何班级最差的小学生的水平,我们不知道单词怎样发音,或应该在什么地方发笑,或演员怎样表演。在这些外国人和我们之间不仅有种族和语言的区别,还有历史传统的巨大鸿沟。奇怪的是,我们总是希望了解希腊,努力去了解希腊,永远感到被吸引回到希腊,永远在对希腊文化的意义提出一些解释,而这些解释是从哪些不相称的零星碎片中得出的,与希腊文化的真实意义相去多远,究竟有谁知道?
首先,很明显,希腊文学是非个人化的文学。约翰·帕斯顿和柏拉图、诺里奇和雅典之间相隔的那几百年构成了一道深渊,欧洲闲话的大潮永远无法到达它的那一边。阅读乔叟的时候,我们不知不觉地乘着祖先生活的水流向他漂去。再后来,随着记录的增加和记忆的延伸,几乎没有一个人物不拥有各自的关系氛围、生活和书信、妻子和家庭、各自的住所、性格、幸福或悲惨的结局。但是希腊人却留在他们自己的堡垒里。命运女神对他们也格外垂青,不使他们落入凡俗。欧里庇得斯被野狗吃掉,埃斯库罗斯被石头砸死,萨福跳崖身亡。我们知道的只有这么一些。我们有他们的诗歌,但仅此而已。
然而这并不完全符合事实,也许永远不会。拿起索福克勒斯的任何戏剧,读道——
当年带领我们攻打特洛伊的那位好汉的儿子,阿伽门
农之子……
我们的大脑立刻开始想象周围环境。它为索福克勒斯设想出某种背景,哪怕是最临时的;它勾画出某个边远的村庄,靠近大海。即便在今天也仍可以在英国较荒僻的地方找到这种村庄,当我们走进去时,不禁会觉得在远离铁路和城市的这群村舍中,具备了完美生活的一切要素。这里有教区长的住宅,有庄园住宅,有农田和小屋,有教堂,有俱乐部,还有板球场。这里生活被简单地划分为一些主要成分。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工作,每个人都为别人的健康或幸福而工作。在这个小小的社区里,个性变成了共同财产的一部分;牧师的怪僻众所周知;高贵女士脾气上的缺陷;铁匠与卖牛奶的之间的不和;男孩和女孩的恋爱和婚姻。这里的生活多少世纪来都按同一条轨道运行;风俗形成了;山顶和孤树上都生出了传说,村庄有了它的历史、节日和竞争。
只有天气难以忍受。如果我们设想索福克勒斯住在这里,就必须抹去烟尘、潮气和湿漉漉的浓雾。我们必须把山丘的轮廓变得鲜明。我们必须想象岩石和裸土的美,而不是草木葱郁的美。有了温暖的阳光和数月晴空灿烂的天气,生活当然立刻就不一样了;一切都在户外进行,所有到过意大利的人都知道这种结果:各种小事都不是在起居室而是在街上争论,从而变得戏剧化,使人们变得健谈,培养出南方民族特有的那种嬉笑怒骂的机智和口才,与每年有一半时间待在室内的民族那谨慎迟缓、低调和内省的忧郁截然不同。
这就是希腊文学给我们的第一印象,那迅如闪电的、俏皮的露天风格。在最庄严和最卑微的地方都能看到。在索福克勒斯的悲剧中,王后和公主站在门口像村姑一样斗嘴,想来是从语言中得到乐趣,把话掰开了说,一心想在言词上取胜。这些人的幽默不像我们的邮递员和出租车司机的那样温和。闲坐在街角的人们的嘲讽不仅诙谐机智,还含有某种残酷的东西。希腊悲剧中有一种与我们英国人的残忍很不一样的残酷。例如,《酒神女伴》中的彭修斯,那位非常可敬的人,在被摧毁之前不是先被取笑的吗?事实上,这些王后和公主当然是在户外,蜜蜂嗡嗡飞过身旁,影子投在她们身上,风儿拂着她们的衣裳。南国的某个明媚的日子,阳光强烈,但空气很令人兴奋,她们在对四周围聚的一大群观众说话。因此,诗人所要想的不是能够让人独自阅读几个小时的主题,而必须是一些有力的、熟悉的、简练的东西,能够迅速而直接地传达给一万七千名目光专注、热切聆听的观众,他们如果坐得太久而没有新的刺激的话,身上的肌肉会变得僵硬。他会需要音乐和舞蹈,并自然会选择像我们的“特里斯特拉姆和伊索尔达”那一类的传说,故事梗概大家都知道,因此积累好了大量的感情,但是每个新的诗人都可以表现新的重点。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