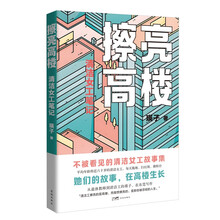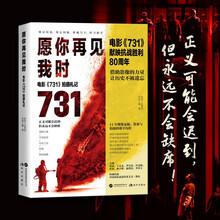她的泪一流,大伯更憋屈,伤心起来自个出村去。他的身后会有好一阵慌乱,紧张兮兮的伯娘会把刚刚进栏的牛从栏里牵出来,将牛绳交在我手上。她明白,只要这头牛跟在大伯的身后,大伯就走不远。
山里路容易看到头却难走到头,年轻人喜欢往城里转悠,老人往山里转悠,总有人找不着回头路。许久以后,人们想起走失的那个人时就会说,只看见过他的背影。
大伯的背影我看得太多了。队里为抓现金收入,隔三差五就挑东西去县城卖。翻山越岭十多里路,我一直盯着他的背影走,上山时,看不到他的头只能看到他黑汗水流的背,衣褂子当是风扇在扁担头左摇右晃。他的背膀有些畸形,瘦长驼背,一条条骨骼清清楚楚,唯两块三角肌山坡似的高高地隆起着,再宽的扁担都能摆平。
他心烦时,背弯得更厉害,脚也不听使唤,一条直路,走得弯弯曲曲。
我完全进入了一个老人和一头牛的孤寂的世界里。不管是上坡下田、在远离村庄的草地上还是傍黑时分稀薄的夕阳里,我们这一老一小总会和一头牛在一起。大伯像我俩的领头,他伤心时,我俩总会在他的左右。很多时候,他跟着一头牛走,我跟着他的背影走;此刻,一头牛紧跟着他,而我傍着这头牛走。牛比我高出一头,当冷飕飕的风划过田垄,荒草的黑影排浪般地扑来时,我紧靠着它,突然感到身在天之涯的孤寂。
牛明白它此时的责任,不急不慢地跟着。两对牛蹄落实了它全身的重量,沉重而又清晰。在荒野的黑色混沌中突现的一抹血红的晚霞里,撩起了一种巨大的寂寞。
往山口走有一座年久失修的木桥,牛蹄踏在架空溪水上的木头时,那种“蹬蹬蹬蹬”的声音像要把木头踩踏似的,让人心惊肉跳。再往前走,我们三个都有可能掉进一个深渊。
人总需要一个解气的结,大伯走上那座木桥时会清醒一半,转回头走到老牛的身边气就顺些了。他终究犟不过这头牛,他担心牛会掉下桥摔死。
一个村庄的黑夜常在一头牛的惨叫声中惊醒。当太阳将山峦照亮、树木农合照黄、鸡鸭遍布篱旁时,有一家牛栏里多了一头小牛。
就像谁家添了一个壮实的小男孩,村里人多了一分聊天的快乐。大伯扛锄下地,经过村口时有意地放慢脚步,弓着腰竖起耳朵,小牛顺产还是难产,是公牛还是母牛,骨架子大不大,都一一听进心里去。和牛在一起时还说:你看人家多争气。
这头牛已经九岁多了,十岁的牛相当于一个步入黄昏的老人。大伯认定畜牲比女人贱,比女人经得起折磨。问或总要说上一句:你再生个崽,让我笑几声去进泥巴。
牛不以为然。这种时候,它通常是甩几下尾巴,以示抗议。
每天的黄昏,全村的牛羊都在草地上集合了。
那是悬崖峭壁下向小树林倾斜的几亩荒草地,没有石头的地方满是匍地生长的无名草,几股山泉在崖底汇合,丁丁冬冬拦腰穿过。草地上花草繁茂旺盛,淡绿肥实的宽边叶、颈长叶圆的马齿苋、浅紫嫩黄的野菊花、白色的牵牛花比比皆是。就像平时不爱喧哗的人,处在山凹里一弯角落,轻松自在,无拘无束,悄悄的生长繁衍。一年四季不管哪个季节,这片荒草地总是生气勃勃。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