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多林瞥了一眼床上的人,说道:“事到如今,您也不必在这问房子里待下去了。”她微微抬头,却没有看费多林,他接着说:“您未婚夫肯定会很快晋升教授,在这方面,人文学科要比我们这行舒坦得多。”他想起多年以前,他也曾渴望踏上学院之路,但他更想活得惬意舒坦些,所以最终还是决定以医学更为实用的一面为业;他忽然觉得在优秀的罗迪格博士面前,自己娃得等而下之。“秋天,我们会搬家,”玛丽安波澜不惊地说,“他已经接到一份哥廷根大学的聘书。”“啊,”费多林说道,想用什么方式表示祝贺,但现在无论如何不是祝贺的好时候。他朝紧闭的窗子看了一眼,好像在行使一个医生的特权,没有征得她的同意就径自打开了两扇窗,让微风吹进来。这会儿的风变得更暖和了,更有春天的味道。远方的树林苏醒了,随风吹来一阵柔和的芬芳。从窗口回过身,他看见玛丽安把疑问的目光转向他。他走近她,解释说:“我希望,新鲜空气对您有好处。天气已经相当暖和了,昨天晚上去。”他原本打算说:我们冒着小雪从化装舞会坐马车回家。但他慌忙推翻句子,改口道:“昨天晚上,街上的雪还有半米深。”
他在说些什么,她根本听不进去。她的眼眶渐渐潮湿,大颗的泪珠滚落面颊,她再次将脸埋进手里。他不自觉地伸手去抚摸她的额头,感觉到她整个身体都在颤抖。她开始啜泣,从几不可闻,继而越来越大声,到最终失去控制,号啕大哭起来。她忽然从扶手椅里滑H{来,瘫在他的脚边,猛地用手臂环抱他的膝盖,把自己的脸紧紧贴住它们。她抬头看着他,痛苦而疯狂的眼睛瞪得溜圆,狂热地呢喃:“我不想离开这里。就算你再也不来,就算我再也看不到你,我也要活得离你近一些。”
他与其说是震惊,不如说感慨;他一直知道她爱他,或者说,幻想自己爱着他。
“请起来,玛丽安。”他轻声说,弯下身温柔地扶起她,同时他又想:这场面真有点歇斯底里了。他瞟一眼她父亲的尸体。要是他能听到这一切,他想。如果他只是僵硬地躺在那里,而神志清醒?也许每个人在过世后的最初几个小时里,灵魂都尚未出窍?他抱住玛丽安,但又保持了些距离,然后自觉有些可笑地,在她额头上勉强地吻了一下。电光火石间,他回忆起从前看过的一本小说,里面有个非常年轻的男人,几乎就是个男孩,在他妈妈的停尸床边,被她最好的朋友诱奸了,更准确地说:是强奸了。在那一瞬间,他不禁想起自己的妻子。对她的怨恨从他心里涌出来,又对那个提着黄色手提箱、站在丹麦的酒店台阶上的男人怀恨在心。他把玛丽安抱得更紧,可心中丝毫没有动情。实际上,她那头干枯无光的头发和潮湿的衣服散发出来的甜甜的腐味,简直叫他恶心。这时门铃响了,他松了一口气,急切地吻了吻玛丽安的手,仿佛带着感激,跑出去开门。
展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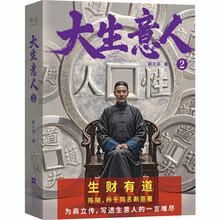
——毛尖
本质上,这是一个关于爱与勇气的故事,充满希望。
——妮可基德曼
施尼茨勒——梦想大师。
——《纽约客》
我通过辛劳的实验所获得的人内心的秘密,你通过日常观察就轻松得到了。
——弗洛伊德写给施尼茨勒的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