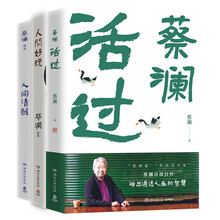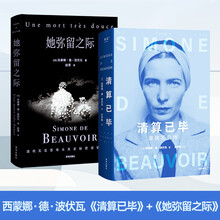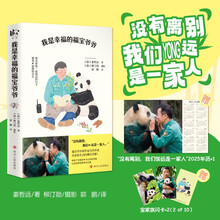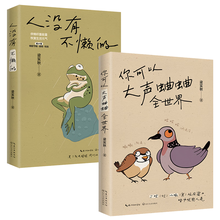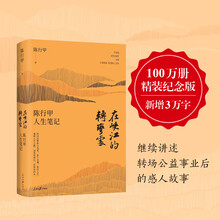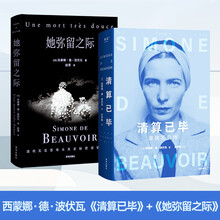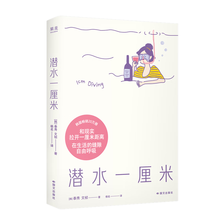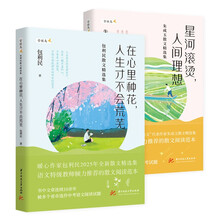曾经被一个女士问道,男人是什么时候开始,把自己的爸爸改称作父亲的?我一时答不上来,想必那是自己也为人父的时候吧?其实,即使在文章里或者在与别人交谈时称及父亲,尤其是在父亲面前,永远是叫爸爸的呀,这难道还有什么疑问吗?!<br> 父母是随我调入深圳大学不久之后的1999年,迁来深圳和我同住的,此前他俩一起在江西生活了四十多年。父籍安徽滁州,母籍湖南汨罗,却都忘不了岭南是他俩的爱情的起跑线。父亲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修粤汉铁路,经过湘东北,认识我母亲,然后将她"拐"了出来。我外公当时应该是有一些田产的小财主,哪里高兴自己的千金被一个来自外乡的铁路穷困小职员蒙走。无奈,我母亲对外公一向的重男轻女忿忿不平,携了两样简单行李毅然启程,随父亲山水兼程一路到了韶关、广州。父亲在韶关铁路工务段待的时间稍长,我姐弟就出生在那里。父亲谈起过的一句相关文学的话语是:杨朔的弟弟在我们韶关工务段。至今回忆那段近似私奔的经历,八十多岁的母亲依然两眼灿灿生辉。我们姐弟看过母亲婚后不久的一张黑白照片,旗袍端坐,烫发螓首,美目丰仪,令我五姐弟一致顿足:造物不公,遗传安在?!<br> 父亲这一辈子,年纪越活越长,地方越呆越小,从广州铁路局、上海铁路局到南昌铁路局,最后呆在赣西的一个叫彬江的四等小站,在那里干了二十年之后,提前终结了自己的工作。之所以提前,是因为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后期还有退休顶职一说,在我母亲的劝说下,他的财务会计一职,由我下乡几年的三姐顶替。现在想来,父亲之所以弃城市而择小镇,主要原因可能是多子女家庭,在城里生活大不易。母亲因为多子女,早年就放弃了工作,后来就没法再进人职工行列,这也成为她终身的憾恨。所以每当谈起左邻右舍的女职工能够吃劳保、有医疗,母亲便不免无限向往。小地方,可以做家属工,挑土方、打石头、装车皮……总之,哪些活累、脏、报酬低,就是家属工——临时工的另外一个组成部分干的,这种临时工扛苦累脏活的现象,一直延续至今。那时候,也是有活干总比闲坐家里强。无论阴晴雨晦、酷暑寒冬,家属工都系着绑腿、戴着草帽、挎着水壶,在采石场、专用线上奔忙。去年我回去看过,一座绵延几公里的大山早已采完,甚至下采几十米。如今都已寂寂如空,只有一些老弱留守。那是不止一代人的青春祭奠啊!<br> ……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