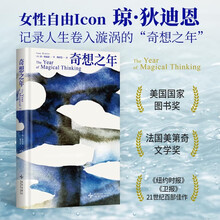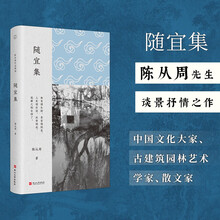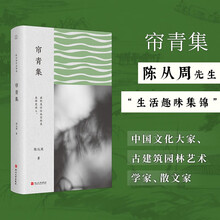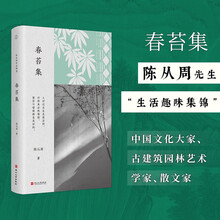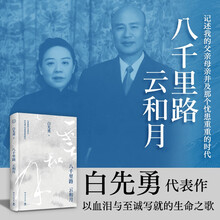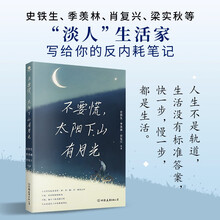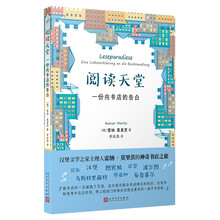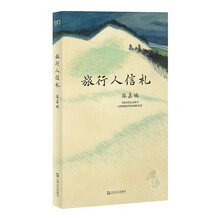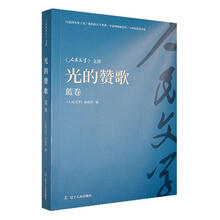回到敦煌
回,是一个亲切熟稔的字眼,除了家,我似乎没有把它给予过其他的地方,然而之于那从未到过的敦煌,我却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回”。
曾经以为,自己爱的是李唐繁华,爱的是汴梁风雅,爱的是把酒临风,吟赏烟霞,一切都应是精彩的。但游历过西安,我却被兵马俑的气势所折服,对秦皇的王者之气心驰神往。游历过开封,我对满目的花团锦簇却丝毫提不起精神来,时隔多年更是渐渐淡忘了。原来,真正令我沉醉的,不是清明上河画繁华,不是人人尽说江南好,而是大气磅礴中吞吐天地的豪情,是睥睨天下、傲视四方的气势,那应该是沧桑的,哪怕破败也没有关系。于是,我的目光自然而然地向西北投去,那里,应该有我向往的沧桑气质。
就是这样一种异于他人的审美情趣把我带到了敦煌。这个丝绸之路上的重镇,曾有“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的万千士卒,曾有“青海长云暗雪山,孤城遥望玉门关”的关口要隘。而另一方面,它却又有“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的醉意朦胧,有“战士军前半死生,美人帐下犹歌舞”的醉生梦死。敦煌,融合了阳刚与柔美这两种奇异的特质,在丝路上迎来送往,转眼就过了千年。西天的梵音从这里传来,商队的驼铃在这里响起,将士、僧侣、商贾,形形色色的人从敦煌经过,他们或“提携玉龙为君死”,或传教度众生。盛极之时的敦煌,俨然另一个京师,即使位于万里瀚海之中,也丝毫不显得渺小,反而隐约中透露出一种帝王之气,迎万千旅人前来朝拜。
也许是因为闭关锁国,也许是因为思想束缚,抑或是因为水土流失,敦煌,渐渐沉寂了下去。如今提起它,人们头脑中蹦出的关键词无外乎颓败、残破。即使是“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的雄浑壮阔也无法掩盖这种苍凉,只会让人们由诗句联想到王维,悠悠地又转到了盛唐。就是这样一个渐渐为世人所遗忘的地方,却使我由衷地向往。正是它的残破,成就了它现在独有的气质。那里,没有现代大都市的繁华,依稀保留着千年前的样子,民风淳朴。那里,没有所谓的旅游开发,时光带走了它往日的辉煌,却留下了废墟和古迹,让我这种喜好怀古伤今的人慨叹。那里的黄沙漫天、大漠茫茫,已经成为它独特的景色,散发着无穷的魅力。那里,远离如今的经济中心,也不需反复地改、扩、建,不像故宫一样被辟成了博物院,不像颐和园一样被改成了公园。敦煌,仿佛一位真正的王室,保留了祖先留下的血脉,冥冥中,似乎还能够再坚守千年。
于是,当已经游历了16个省市的我将敦煌定为第17个目的地的时候,内心深处隐隐有了一种回归的感觉。当我即将可以骄傲地宣布:“我已走过了半个中国”时,当我终于要去探寻敦煌时,我忽然难以抑制地激动起来。这种感觉,即使是第一次踏出国门也未曾有过。很久以来,我从没有如此渴望地奔向一个地方,一向在人前十分安静的我,竟也能那样激动而自豪地向好友宣告:“我要去敦煌”。
当飞机离开了北京,一路向西飞去,当窗外终于出现了一望无垠的沙漠,当我终于踏上了敦煌的土地时,我几乎要欢呼雀跃起来。这是一种最自然的喜悦,这是一种最原始的快乐。因为我知道,我必将在敦煌远离都市的喧嚣,在敦煌找寻祖先的影子,在敦煌领略自然的壮阔,在敦煌探访心灵的归宿。终于,那个生活在快节奏的都市却经常为几句诗词走神的我,那个“义愤填膺”慨叹“人心不古”的我,那个喜爱废墟古迹看淡琼楼玉宇的我,总算是来到了最契合自己心中想象的圣地,总算是看到了梦寐以求的景象。
我回到了敦煌。
……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