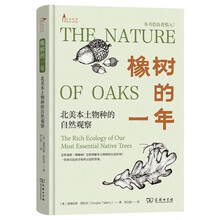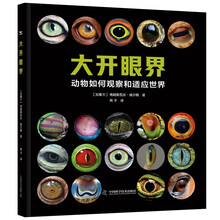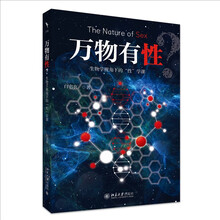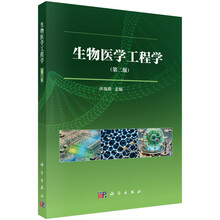一、天使鸟儿万里咸至(鹤飞篇)
浩浩南迁
初冬的天际,一层薄薄的雾霭漫开在整个目所能及的世界。左边是大海,那蔚蓝还是那么千年万年不变的蓝,遥无边际地与天光的分界线相接。长空里看海,海是平坦的,没有人们近在咫尺看到的那种惊涛骇浪。右边是平原,是山峦,青翠的麦田被纵横的阡陌分解成长方形、正方形。河流是银亮的白线,时粗时细,支流和主流组合成清晰的线网,如身体中的血脉,直伸到那一片片丛林和山体的结合处。山峦高耸,静静地观望着世间的四面八方。茂密的林带装饰着山峦,使它们的体态那么丰满,而不是裸露出瘦弱的脊梁。在陆与海激情的交吻处,界限分明,印痕连绵延伸,一直向前,时而凹时而凸,时而大幅度弯转,时而小距离回曲。沙滩上的白色线条是海与陆激荡起的浪。几千年、几万年了,海是博大浩瀚的伟男,陆是羞涩多变的女子,它们相依相爱,情愫缠绵,始终没有完结的日子。天国的鸟儿飞来了,它们背负着兴安岭的茫茫林海,背负着长白山的冰天雪地,背负着蒙古大草原的草场银湖,背负着西伯利亚的寒风冰原,日夜兼程向南飞翔而来。
素羽嗷然,偶影翔集,大群的丹顶鹤自然分成几组,组与组间没有明确的分别标志。时而几组相联成阵,连绵几公里长,鸣叫声此起彼伏,相告着各自的存在。时而几组相联横排,一齐向前,每一群心中都有一个目的地,每一只心中都向着这次长途的终极目标。
在飞行的旅途上,丹顶鹤是不知疲倦的神鸟。那轻盈的体态,由侧面看去,神鸟的头喙前伸,脚尽力后伸,略有下垂,身子成一个近似平行的流线。羽翅一上一下,有时一起扇动,用力地下压身边的空气,有时缓慢地机械地扇动,显得悠然而神逸。羽翅起落的频率可以慢慢数清。如果你从神鸟的后面看去,它们每一只的羽翼又都像一张长弓,一张尚未拉满的弦线悠长的长弓。
神鸟群奋力地飞行,向南再向南,带着天国的嘱托,带着天国的语言向南远行。一对丹顶鹤在距群鸟后几十公里处飘逸地飞来,沿着大队飞翔的路线,只是比它们的航线要高一些。早晨飘落的雪花湿润了鹤背上的羽毛。阳光照过来,每一只身上蒸腾起不易察觉的淡淡水雾,融进蒙蒙的雾霭里。它们的故乡,向北是那片宏阔的湿地,向南是东海边广袤的苇丛。一年一度,神鸟来往于两地,真正的寒冬似乎离它们很远。
天宇澄旷,鹤群中有一对相邻地飞翔,雄的叫霄霄,雌的叫凌凌。霄霄十分呵护凌凌,它在羽翅上仰时,侧过鹤颈从右翅下看看凌凌,凌凌也常常从扬起的左翼下隙处用左眼的余光望望霄霄,还一声清脆的嘎嘎声。霄霄也总在此时不失时机地回报一嗓嘎声,声音中比凌凌呜叫更多了一些浑厚。有时霄霄会有意放慢羽翼的扇动,落在凌凌身后,看看凌凌身后伸直的黛黑的脚,那裸露的脚不会冷吧。有时霄霄会紧扇双翼,飞临在凌凌上方,下俯凌凌奋飞的姿态,很想为它助上一羽之力;有时霄霄又会落到凌凌的下方,上仰起头,看凌凌优美的翔姿,为它的倾尽力量向前的姿势欣慰,因为前方有它们的共同理想。更多的时候,霄霄飞翔在凌凌前方,为凌凌提供一个减少气流阻力的小角,使凌凌减少体力的消耗。它们的父母兄弟也总是在队伍的前面,奋飞向前。
风突然加大了力度,从右侧刮来,鹤群的前后一字形被风向左平移了几十米,领头的鹤坚定地向前,身后的队形很快调整为一条顺风的斜线,继续前行。风又小了一些,太阳在朦胧的天光下缓缓地滑向西天。看不到太阳明晰的轮廓,只是感觉到它那光明聚集耀眼的地方。鹤群要继续飞行,霄霄知道它们的目的地已不会太远了。
天光有些黯淡起来,鸟云越集越多,整个天穹呈现出淡墨色。鹤群身下的田畴、阡陌、河渠、山林间闪亮起了一盏盏灯火,或星星点点,或密密集集,像由天上撒向人间的夜明珠儿。
天色更加暗下来,云层在鹤群的上方飘浮,已聚集得越来越厚如抹不开的浓墨。鹤群又向下降低了许多,但不至于挨上那地面上的楼宇尖顶或一闪而过的高架铁塔、黑烟滚滚和白烟缭绕的烟囱。轰隆隆、轰隆隆,闪电划开了鸟黑的云层,照亮了依然飞行的鹤群,就像一条耀眼的白练。轰隆隆、轰隆隆,霄霄和凌凌感觉头上、颈上有雨点轻轻击打。蓦然间,雨点越来越密了,击打在双翼上,它们看见了闪电下羽翼溅起的雨珠在飞,鹤群没有降落,一直向前,很快冲出了雨层。
鹤群上方的鸟云变得薄起来,夜空也变得清亮起来,也许是天雨洗净了天空。透过云层可见云上的那轮明月,可见夜空里的星辰。霄霄、凌凌身上被雨淋湿的羽毛也慢慢变得轻松,不像刚才那么沉重。终于,头鹤降低了飞行的高度。好闻的海腥味袭来,在一片片阔大的苇田滩涂上空,头鹤领着它们停止了前进的飞翔。它们开始盘旋。水光倒映着天上的星辰、倒映着明月。芦苇摇动的沙沙声传来。已先于它们而来的鹤群在刈过的空旷的苇田里鸣叫,似在迎接着小队鹤群的到来。霄霄在前、凌凌在后,它们降低着高度,滑翔着,羽翅静止地与地面越来越近。它们两脚叉开,羽翼伸长着接触了地面。双脚有些麻木,在草地上向前跳动几下,收住了羽翼。鹤群开始大会师。霄霄和凌凌兴奋地和着鹤群,一起伸长脖颈欢唱着丹顶鹤的欢乐颂。
湿地仙禽
鹤的命名源于人类,而鹤的起源又要比人类早了六千万年,鹤和天鹅、大雁、野鸭以及世界上九千七百八十七种鸟一样,它们的共同祖先是始祖鸟。在辽宁省朝阳市北票四合屯发现的原始祖鸟、在欧洲发现的始祖鸟或许是它们的祖先,而那些祖先生活在不可思议的早白垩纪,距今已有一点五亿年。最早的古鹤类生活于新生代第三纪的始新世。中新世的旧大陆上古鹤类、原冠鹤类和中新鹤类已是家族兴旺。地球变迁,新大陆形成。鹤科又分两个亚科,即冠鹤亚科和鹤亚科。考古发现,冠鹤亚科的化石属于三千七百万年至五千四百万年前的始新世,已知有十一种冠鹤生活在约五千万年前的欧洲和北美洲。
原冠鹤和加拿大鹤大约生息在四千万年前。那时,地球的北部大陆气候温暖,湿地连绵,是鹤类最初的伊甸园。三十多种鹤欢聚在树林里、沼泽中,几千万年在万物赖以生存的地球变迁中转瞬过去。地球内部的躁动,连绵不断的造山运动,隆起了阿尔卑斯山、喜马拉雅山、落基山和安第斯山,地球像裸露的野人穿上了衣服,一个粗犷的汉子似乎正渐渐地起来。但它的野性时常爆发。第四纪冰川铺天盖地而来,无情地毁灭它的大批子民,大片的湿地被没有生物痕迹的冰川和突兀的大山取而代之。温暖的气候被无情地挤走,美丽的冠鹤栖息地也被无情地压缩到非洲那紧临赤道炎热的地方。地球北部悬殊的变化,各种残存的鹤类在不同环境里进化。遥远的四千万年前,三十多种鹤减灭了一半,冠鹤亚科仅有两种在非洲中南部幸存下来。鹤亚科化石最早见于中世纪,约五百万至二千四百万年前,七种已灭绝,现尚存十三种。在鸟族这个大家庭里还有十五种鹤飞翔在世界各大洲。
霄霄、凌凌它们这个大家庭一时热闹起来。夜风轻轻地吹来,摇动了水边的苇。呱呱、呱呱,野鸭在喧闹一番后又恢复了平静。咚,有鱼企图跃出水面又被水亲密地收回。或许那是条鲫鱼,被黑壮的鸟鱼追逐,但霄霄不知那鲫鱼能不能逃脱。
霄霄知道,在这个大家庭里它们不会孤单。它曾和白枕鹤擦肩飞过,白枕鹤一身的灰白,颈背和喉又是白色,伸长的腿是很美的绯红,一脸红羞的它怕见生一般,匆匆地飞去隐进了苇丛里。有次霄霄和三只灰鹤在苇荡边觅食,灰鹤披一身灰色的大氅,眼后的白像画上去的一直抹到颈背。灰鹤头上也有像霄霄一样的红顶,不过又要小得多,而且周边被黑色包围显得小气。霄霄还和个子小些的白头鹤邂逅在一个苇荡里。白头鹤那白色的头顶前黑中有红,颈部洁白,与全身的黑反差鲜明,那黑黑得深沉,霄霄也很喜欢。霄霄记得在遥远的北方,它们还和蓑衣鹤一起飞在大草洼上空,蓑衣鹤蓝灰色的身羽是那么优雅,颈上、胸上的黛黑垂得好长,像披戴的蓑衣,头上的白色长羽披散开来颇有种浪漫情调。霄霄最欣赏的还是那群白鹤,它们展翅飞翔时,“分行似度云,扬影疑翅雪”,除那羽尖像蘸过墨,全身是一尘不染的洁白,腿露两支粉红,颊也红得很美。那年,霄霄还在一群野鸭中见到一只形单影只的沙丘鹤,那鹤颊上施着粉白,头额鲜红,全身的灰衣显得它娇小秀气,羞于见生。它是怎样与家族失散飞来的,霄霄也不想知道。在中国,还有霄霄没有见过的赤颈鹤,它身高体大,红颈红脸红腿,全身灰黑,唯有在几千里外的西南边陲和高峻的喜马拉雅山脉以南才能见到它们的身影。
在世界鹤类的名册上,十五种鹤在中国即有九种。也许那美丽的美洲鹤、非洲的肉垂鹤、澳洲的澳洲鹤,还有中非和西非的黑鹳鹤、南非的蓝鹤、东非的灰冠鹤、北美的加拿大鹤(沙丘鹤)都很难与中国的鹤相遇。它们天各一方,坚守着自己的领地,流连于自己的家园。灰冠鹤的头饰异常地美丽,黑头,白脸,浅蓝灰色的颈,脸上方、头颈下红色肉垂异常鲜艳夺目,最奇特的是头上一大丛散开的金色头冠,如金光熠熠的王冠。非洲的冠鹤还遗存了几千万年前鸟能栖树的特点,是唯一能夜栖于树上以避猛兽的鹤了。
那只与霄霄相识的沙丘鹤知道,它的家族是世界上最大的鹤类家族,主要生活在北美。它们群飞时如遮天蔽日的鸟云,它们落水即能遮住一片片明亮的水塘。它们不像其他家族已寥寥可数、岌岌可危,而是浩浩荡荡、颇为壮观的六十万只的大军团。霄霄知道,最美的还是自己的家族,它们脸颈是黑色,次级、三级飞羽也是一片黛墨,收起羽翅时黑色聚拢在尾部,如穿上一身洁白的衣裳配以黑色超短裙。腿修长而黑,亭亭玉立的姿态,优雅动人。耳羽后的白色带直至颈背,头顶那一圆彤红灼灼夺目。
那是近半个世纪前的初夏,还是懵懂少年郎的我从四千里外的川南来到渤海边。看惯了高峻嵯峨、连绵起伏的青山的我,在这片坦荡广袤的大草洼边,惊愕地停下了脚步。从此,命运把我留在了这片神奇苍茫的土地上。
春来,听着大雁声声,看群群候鸟由南方翩翩飞来;夏归,走进大洼听鸟儿伴着鱼跃声无休止地喧鸣;秋至,在芦花飞扬的大洼上空,看鸟儿俯仰群翔,为南迁试飞着劲羽、计划着日程;冬临,听盘旋的苍鹰在簌簌寒风中的羽翼振动声,和那些喜鹊、麻雀等留鸟在雪原中略显孤寂的鸣唱。大洼边,我偷看着鸟儿缠绵交欢,听着它们喋喋私语声长大;大洼边,我追逐着鱼儿,听着它们水中的嬉笑声长大;大洼边,我数着飞来的丹顶鹤和天鹅,听着它们高亢的歌声长大;大洼边,我荡着小船,听着船儿擦过苇蒲湿润的声响长大。
第一次见到丹顶鹤,就是在南大港这个大草洼。早春,寒凝初开的大洼绿水荡漾,三只丹顶鹤落在大洼的深处。不远处还有十几只天鹅相伴。凛凛大气的丹顶鹤散发着美丽的神采,或洗浴、或梳翎、或觅食,高雅中透着神逸。我敢说,那是最有魅力最有气质的鸟儿了。从那年起,每年春,我要去大洼看丹顶鹤,或是打电话问那里的朋友:丹顶鹤飞回来了吗?十几年了,寄托着我年年的牵挂,年年的久盼。
于是,对鸟儿的喜爱常在我心中萦绕,对鸟儿的情怀也就不断由笔端落在纸上。画家用线条和七彩描绘洼里的鸟儿,而我却用祖先留下的几千个汉字描绘鸟儿。洼里鸟儿的舞姿、鸟儿的鸣唱、鸟儿的情爱、鸟儿的靓羽,还有那鸟儿与人割舍不断的情意和愤懑。一齐在纸上飞扬着。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