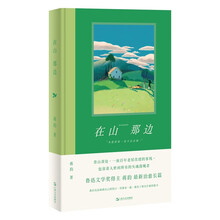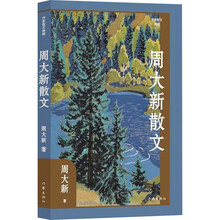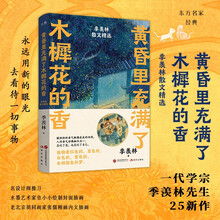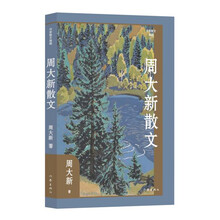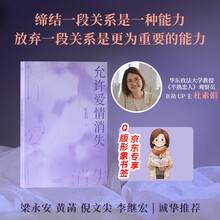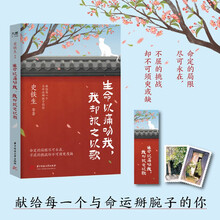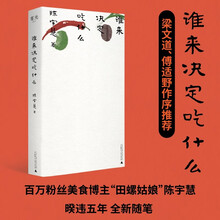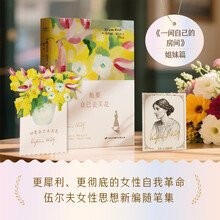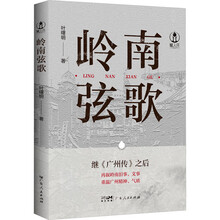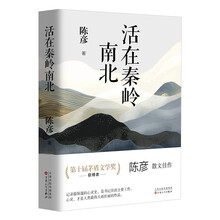诗里的第二联:“笔铨典著文堪艳,根索辽源路始通”,在精心对仗的句子中,说出了先生对于我们治学坎坷之路的心里话。前一句是讲我,用力于鲁迅著作的研究,仅仅是取得了一点微不足道的成绩;后一句是讲张菊玲,由用心于收集明清小说批评的史料开始,后来,进入对于满族文学的研究,终于走出了自己的学术路子。先生对于自己学生关注的深情,鼓励和期望的殷切之心,闪烁于诗句之中。前两年,这首诗在《光明日报》上发表的时候,不知是谁给加的注解,依据其中“根索辽源”一句,说我“近习满文”,弄得一些朋友或见面,或写信,正经八百地问起我来:“你满文学得怎么样了?”我哈哈大笑。这也算是由先生的诗引出的一个插曲吧。<br> 先生的墨迹,经荣宝斋精致的装裱,一幅淡黄色的长轴,朴素、高洁、大方,至今挂在我们书房的墙上。此时再看这个条幅,声音犹在,墨迹依然,人却永远地离去了!<br> 吴先生晚年,亲生的子女都不在自己身边。只有一个外孙子与他住在一起,也很忙,没有办法更多地照顾他。我们作为学生,曾经几次提出,要不要把哪个孩子调到北京来。吴先生都非常干脆地拒绝了。他总是说:“孩于是国家的,是党的,不是我个人的。他们都有自己的事情要做,不能叫他们放弃自己的工作,来陪着我这个没有多少用处的老人。”先生还说:“我是共产党员,我不喜欢像有的人那样,总想把自己的孩子都弄到身边来。”吴先生最反对说假话,他的这些话里没有一点儿矫情。他完全出自真心。严于律己,这是先生一贯恪守的人生准则。<br> 唐山地震时,他的最小的儿子葆刚夫妇在那里当教员。两个孙子都不幸遇难了。我们知道,吴先生心里是很难过的。但他没有提出任何要求。我们谈起这个话题,他反而安慰我们说:“人生一世,经历的天灾人祸,多得很。
展开